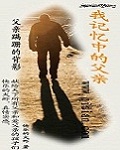烙刻:记忆中的影像-第2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期间也屡获各种奖项。现在家里安度晚年。
吴先锋当了全国人大常委后在当地被任命为广东省团委副书记,后来又是海南八所港务局党委书记。吴先锋后来找到了可心的姑娘,在三亚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后来据说又转到南京工作。以后伍振超就和他失去了联系。
时光就像海水,淘尽了许多东西,留下的是最坚硬的石头和最柔软的记忆。
长城第一照
如今的长城照片已经到了泛滥的地步,但所有照片的知名度加在一起,似乎也超不过这一张。
联合国总部大楼大厅里挂着的高5米、宽10米的巨幅壁毯,上面的长城图案,就是按这张照片的画面制作的。它峰峦叠嶂,山色多变,曲折萦回,气势磅礴,已经成为象征新中国的一个重要国际符号了。
这幅照片从1962年诞生至今,已经在画册、报纸、杂志、明信片、织绣品、日用品、纪念品等无数种载体上无数次出现过。从传播的角度讲,《巍巍长城》绝对称得上是“长城第一照”。如果按今天的稿酬标准,这一张照片就足以让作者成为百万富翁,甚至千万富翁。
这幅照片的作者是《人民画报》社的著名摄影家何世尧。1962年的秋天,在何世尧的老师、著名摄影家敖恩洪的带领下,一行人马乘车来到了八达岭长城脚下。那时的长城没有这么多游人,没有这么多汽车,也没有这么多大煞景色的建筑,整个八达岭也只有几处稍加修缮后对外开放,长城显得自自然然、干干净净。到了长城上,大家分头去寻找自己的拍摄角度,都想拍出不俗之作。何世尧早就发现,已有的长城照片,多是站在长城上拍长城,尤其是早晚光线下的长城照片为数不多。这也难怪,别说那个年代的生活水平、拍摄条件与如今有着天壤之别,又有多少人能够摸一下照相机呢?作为建筑兼意识形态符号,那时候天安门与伟大领袖紧密相连,长城则与劳动人民密切相关。20岁出头的何世尧虽然是《人民画报》摄影记者中的小字辈,但他心里总想着要拍出一张像样的长城照片,他甚至具体想到,要拍一张“一抹朝阳染红燕山峰巅,长城在灰蓝色的群山中隐约盘旋”的作品。这次,他背着沉重的相机,走出了长城,他想到那边的山头上看看效果,几经爬山观察,终于,那个冥想之中的画面出现在何世尧的眼前!
1962年的8月,我和敖恩洪老师还有我们画报社的另两位记者一道去了长城。这次报道长城的起因是人民画报想系统地、比较新颖地介绍长城。我们几位编辑记者事先翻阅了过去报道长城的报刊,做了许多准备工作,编辑也给我们几个讲了他的想法,最后我总结了就是那两条:一多一少—“站在长城上拍长城的多,早晚时分拍长城的少”。所以我就尽量要找到长城以外的角度。本来我想拍一张早晨阳光漫射、山体蜿蜒的长城。所以大家说好要早一点出发。那时候我们几个年轻的都住单身宿舍,司机就和我住在一个屋。果然,我们按计划天不亮就出发了。那时候路上人少,车也少,社里派了个波兰产的华沙牌小车,日出前就到了。到那才发现,我们全错了。因为长城是在山上,所以日出时山里还是黑暗的,长城更是什么也看不见,等太阳照到长城时已经是上午9点多钟了!哪里还有什么“日出长城,朝霞漫射”?
希望就放在下午了。我们几个中午简单吃了点东西,下午就各走各的了。我开始往东爬,打算从东往西拍。半道看见敖老师坐在石头上,大概是他岁数大了,走累了。我向他招招手表示我在这里,他赞赏地点了点头。他一向鼓励年轻人去创作,这次来也是这样。
上午我已经拍了几张,但都不理想。到了下午3点多,我突然发现了一个角度,是在长城之外,那个冥想中的画面马上就要出现在我的眼前!角度是找到了,算是有了“天时”,但似乎还美中不足,于是我就架好了林好夫相机,装上了180mm的镜头,满满地把长城装了进来,耐心地等候。一直等了两个多小时,大概在5点多时,“地利”出现了。这时的长城,蜿蜒曲折,夕阳把长城照得轮廓分明,空气中弥漫着暖暖的光线,山体的几起几伏让我十分激动,我开始拍。那时没有那么多胶卷,觉得好了就按一张,过一会儿又按一张,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拍了6×9的反转片整整一卷!天色将晚,我带着兴奋劲儿往山下走,几路人马都会合了,大家各自交流着体会,车停在那里,已经没什么人了,现在从画面上看,还能看到我们的那辆车。一路带着兴奋和疲劳回到城里在新街口那里吃了担担面。
。 想看书来
《西沙民兵》:红光亮的代表作(3)
一卷只有8张,要知道那时在同一个位置拍8张是要受批评的。结果回来一冲,不但没挨,还得到一致肯定。当年在《人民画报》上一发表就引起好评,此后就连续被采用,直到今天,还不断有各种媒体在约稿。
后来这张照片用得多了,底片也褪色的褪色,划伤的划伤,为了抢救这张作品,我根据当时《中国风光》大画册的色彩,自己复制了一张负片,再根据新华印刷厂的打样放出一张标准的照片,再把这张照片翻拍成反转片,总算有了个底片。现在外面的约稿都是根据这些底片放的。
后来社里的同志们让我再去拍,我也想再去看看。结果又去了两次,角度是一样的,但怎么也拍不出第一次的感觉了。再后来也有别人去拍,但是都没有同样的效果了。这一点我也很疑惑。后来我研究出来,原因是那造成远近山体隔离感的微微雾霭难以遇到,没有那样的光影了。季节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冬天或夏天都不行,只有在夏末秋初才有这种效果。所谓“天时”可遇不可求。
1974年中国政府送给了联合国总部两件礼品:一是按照何世尧这张照片织绘的长城壁毯;二是“成昆铁路”的牙雕。去过联合国的朋友回来告诉何世尧,说你那个“长城”在美国挂着呢。还有朋友去瑞典回来说,你那个“长城”人家印在背心上了。在那个年代,人们基本上没有著作权、版权这类概念,连人都是党的、国家的,何况一幅照片了,所以署名问题、稿费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了。
对于《巍巍长城》,著名的邮票设计家邵柏林曾说:谁能拍出众人皆拍又众人皆无的作品,那才叫真正的艰难。何世尧的《巍巍长城》,客观上把拍摄长城的标杆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意味着他给别人出了难题,也给自己出了难题。还有评论说,何的《巍巍长城》盘亘而上,弯弯曲曲,绕遍群山,辉耀穹宇,就像中华民族悠久的发展史,曲折明晦,悠然远去,化入无极。
何世尧本是画报记者,最长于拍摄社会题材的专题报道,后来他走上了风光摄影之路,成了著名的风光摄影家,与这幅照片的成功有着很大的关系。对于拍摄长城,何世尧认为:“作为一名风光摄影家,长城应该是首选目标。除了北京的长城外,还有各地的长城,石头的、土的,形象极为丰富,有拍不完的内容。现在有些摄影家把长城研究得很深,把长城的阴晴雨雾都了解得很透。我相信,以后还会有更好的作品出来,长城是一个取之不尽的艺术源泉。”
“最高”的照片(1)
在我采访的摄影名作作者中,有两位不是摄影家。一个是拍摄林彪飞机坠毁现场的外交官孙一先,另一位是拍摄中国登山队攀登珠峰的登山队员侯生福。
以专业摄影的眼光看,这张照片在技术、技巧方面没有任何值得夸耀的,甚至连清晰度都有问题。这张照片的价值在于:它是中国人征服世界第三极—珠穆朗玛峰的证明。
如果说登山是个险峻的事业,那这张照片就是这个事业里程碑式的徽章。
这张照片是1975年拍摄的,其实早在1960年中国登山队的王富洲、贡布、屈银华就第一次从北坡登上了珠峰,但那时缺乏经验,登顶时是在夜间,没有留下任何影像资料,致使国际上很多人都不承认这次壮举。回忆当时的情景,侯生福讲:
山上都是冰雪,而且风很大,风速甚至可达每秒60多米,而12级台风才每秒30多米。常有登山者被刮得无影无踪。山上还缺氧气。一般讲,3000米以上人就有反应,头痛呕吐没力气,胸闷腿软失记忆,直至死亡。有的运动员往8000米高峰运送氧气瓶,结果到了地方后又原样运了回来,这就是因为失忆。
珠峰不是平地,而是峭壁千仞,冰川纵横,不时还有雪崩,风雪来时什么也看不见,大家只好用绳子互相连接起来。四五个人一组时,有一个人掉下去其他人还可以拉上来,而要是半数以上的人掉下去就惨了。
1983年,《陕西日报》的记者张东看到了昔日的登山英雄如今却在一个县体委的传达室看门,就写了个内参给省领导。很快就有了回音,侯生福被提为县政协副主席,在这个位置上他一直到1999年退休,再也没变化。如今他的住房仍然是50多平米,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媳也已下岗,儿子因患心脏病花了不少钱。当年他们登山成功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隆重接见,包括华国锋、邓小平等,那是1975年,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都处于重病折磨下,没能接见他们,许多队员都哭了:“毛主席和周总理没病的话一定会见我们的!”
现代登山运动发源于1786年。法国科学家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一个村子里贴出告示:凡能登上勃朗峰之巅或提供线索者,重金奖赏。那时的登山纪录是4810米。此后,纪录被不断地刷新。1950年,英国人从南坡登上了珠峰,到1960年,世界上8000米以上的山峰有13座已经被各国登山者征服,而登山者的名单中没有中国人的名字。第14座山峰就是在中国境内的西藏聂拉木县的希夏邦玛峰。此时中国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中,但是也下了决心要接受挑战。
我是1939年出生的,祖籍陕西洛川县。1958年入了伍,1959年被派到西藏去参加平叛,一年以后我就被选进西藏登山营。营部叫我去,问我想不想登上珠穆朗玛峰?我说想。他们又问登山很危险很辛苦,还有牺牲的可能性,你怕不怕?我说当战士就要不怕牺牲,为国争光,只要能登上珠峰,死而无憾!我们那个团只有我一个人被选上。我们一共有50多个队员,三分之二汉族,三分之一是藏族。营长告诉我们:西藏登山营的任务主要是挑选后备人才,建立队伍,培养高水平运动员。
当时的背景是,为适应世界登山运动的发展,国家体委考虑要在外省市建立一批基地,为中国登山运动和世界探险登山作出贡献。而西###特的条件是得天独厚的。登山营成立的那个周末,西藏军区和体委的领导来看大家,吃了一顿丰盛的晚宴,在三年困难时期,这样的饭菜并不常见。
事实上,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他们就是顿顿水煮土豆干白菜,而同期拉萨市民每月只供应二两肉。管给养的人天天找吃的,但是大家都困难啊。这样的伙食别说登山,就是温饱也马马虎虎。
登山营里有男有女,虽然生活艰苦,但大家却十分快乐,我们还种菜,我种的大葱每根重达一斤多,是队里的冠军,这是登珠峰前的一项“纪录”。后来登山营从120多人减到50多人,再后又减到了40多人,我总是被留了下来。我们自己种地,盖房子,训练,再苦再累不怕,就怕吃不饱。
1965年,我成为西藏登山营的教练,但我还没登珠峰呢。虽然没登,训练却是大量的艰苦的。每天负重跑步,攀登,打绳结,用冰镐,练摄影技术,观气象,学医务知识……总之,既像运动员,又像科学家,一个人要当几个人用。
1964年5月2日,中国登山队登上了希夏邦玛峰,许竞等10人征服了希夏邦玛峰,尼玛扎西用冰镐在峰顶上挖了个小坑,把毛主席像和国旗、顶峰签名等放在了里面,永远地留在了雪山上。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我被授予了一级登山运动员荣誉奖章。那个宴会厅太大了,2000人的宴会,我一晚上睡不着,咱一个贫苦农民之子,仅仅做出这么一点成绩,国家就对咱这么好,我一定要用自己的热血报效国家。回到家,我跟家里人说,他们都不信:哪有万人大会堂,2000人宴会厅?其实是5000人的宴会厅!
有了登希夏邦玛峰的成功,就有了登珠峰的决心。从1965年开始,登珠峰的各项工作就进入实质阶段了。我们的侦察队到达了7000米的高度,为贺龙元帅提出的“三年内要从珠峰北上南下”的计划作准备。时间预定在1967年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