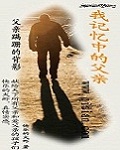烙刻:记忆中的影像-第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些底片的下落是个问题。在编辑《人民的悼念》这本画册时,底片都交了,后来新华社也复制了一部分底片给我们,现在我手里只有这张原底了,因为就这一张拍了3张。其他的不知去向了,有的也是几经辗转,磨损得很厉害。但我认为,就这个事件来讲,它们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我也知足了。
“四月影会”连着举办了三次展览,每次都引起轰动。这批青年摄影家也渐渐成熟起来。后来这个团体改名为现代摄影沙龙,再后来又改为当代摄影学会。每次改名都更加理性,这些工作王立平都参与了。而这个时期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阶段,文化氛围越来越浓,王立平必须在他的本行—音乐上有所作为。事实上,这一时期也是他创作的旺盛时期。他的那些脍炙人口的作品流传甚广,结果一个音乐家的王立平频频出现在大众面前,而摄影家的王立平则淡出了大众的视野。尽管这样,王立平的摄影情结并没有消失,至今他还没放下相机,屡屡以嘉宾的身份出现在摄影活动的现场,手里举着最新款的数码相机。我在他的抽屉里看到,起码有4台数码相机,家里的苹果电脑中存着他最近出国拍摄的大量照片。从中国电影乐团团长的岗位上退下后,王立平担任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而且是专职的,他还是全国人大常委,如今政务缠身。他还创建了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保护了数以千计的音乐家的合法权益,如今,这个协会的收入以每年数千万元的速度增加,再次体现了他卓越的组织才能和博大的胸怀。
见过王立平的人会发现,他很好相处,性格开朗,多么大的事情,他总是娓娓道来,充满智慧。总之,你会觉得,他和你在一起。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吴鹏:端着相机的“四五英雄”(1)
如果说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期间还有一些人是出于凑热闹、发烧的角度在拍摄的话,那吴鹏、王立平、罗小韵、李晓斌等一批“摄影有识之士”就已经是明明白白地认识到了这个重大事件的含义,认识到了必须用相机来记录这个重大事件。他们将个人的安危搁到了一边,拍得了一批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照片。
吴鹏是个大“烟筒”,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而且只抽一半就掐了,让我这个不抽烟的看着好生浪费。他现在是中国摄影家协会的展览部主任,坐在到处都堆着照片的办公室里,一向不爱说“这些事”的吴鹏渐渐打开了话匣子。
我有三次差点被抓进去。
1976年4月2日,有个便衣跟了我很长时间了,最后他抓住了我,要收相机并且让我跟他走,还在广场上当场审问我。我就不服,跟他顶。这时围上来好多人,大声说“不许带人”,“我们悼念总理怎么啦”?本来我在拍照,大家以为我是便衣呢,这下大家认为我是“自己人”,马上就对我好了,这一起哄,那个便衣也没辙了,只好走开。这一次是大家救了我。
4月3日晚,正好“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那首诗刚贴出来,大家都在那里朗诵和抄写。我也在拍,晚上9点多钟,突然一大批士兵和警察们把大家都围上了,当时只有十几个人,正好在纪念碑东南角,我们都动不了了。这时警察开始调来后开门的吉普车开始装人,一次装几个,我尽量往后褪(音tun),结果就成为第三轮被装的。这时纪念碑北侧又有情况了,有人在喊,从我们这边调兵。走了一拨儿又来了一拨儿新的,到该带走我时只有五六个人了,正好我面前站的是个新兵,我就急中生智,大声问:“这儿怎么了?出什么事了?”那战士看了我一眼,问我是:“干什么的,你从哪儿来?”我说我找自行车呢。那你快出去吧!就这样我又逃了一次。
还有一次是在4月5日,就是被命名为“四五”的那个晚上。
那天晚上,我也在广场,突然有很多士兵和警察出现,并从大会堂、历史博物馆,还有南北两侧开始往广场中央收拢。大家都在跑,而且都是朝着南面稍微宽松的方向跑。我也跟着大家跑,就听见有人喊“抓人啦”,当时有个北京冰箱厂的工人(那是他自己告诉我的,因为那时大家都尽量避免问对方的名字和单位)建议往南跑,结果到了南边,南边也有人封锁,正好有一辆20路公共汽车路过,警察让车子赶快走,我们几个人就借着汽车的屏障跟着车跑出了广场,就听警察在后面喊“站住”,这会儿哪能站呢。我一口气跑到北京饭店才敢停脚,算是又漏网了一回。
后来市公安局里的照片我也看到了,总共有三大麻袋。那里大部分是从各个照相馆里没收或从各处搜集起来的,好多是人们在天安门的纪念照片,而其中就有我的,可见我早就被盯上了。当然后来我能看到照片,说明对这件事已经是平反了。实际上,像罗小韵、王立平、李晓斌我们这些人,早就知道不能到照相馆里去洗,而且在这之前我们自己都会冲洗,所以关键的照片就这样留了下来。
那个年代有照相机的人不多,当时专业记者们也不能公开去拍,于是,这些业余摄影爱好者就赤膊上阵了。他们拿着档次不高的相机,里面装着从电影厂里淘换来的黑白胶卷或者是几角钱一个的国产“代代红”卷,凭着一颗火热的心和一双敏感的眼睛,拍下了数以万计的照片,终于使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没能成为影像的空白。
那会儿我用的是基辅相机,我开始学摄影时就学修相机,所以对相机比较了解。买来10米或20米电影胶片自己装盒。我第一次去广场是1月8号。刚一听广播知道总理逝世我就去了广场。那时人还不多,所以拿相机的就很显眼。我那时在北京丰台当铁路工人,为了拍照方便,我宁可上夜班,腾出白天来去广场。别人怎么样我不知道,我是很明白为什么去拍摄的。而且从技术上讲,我已经没有问题了,只要能拍,我肯定能拍到好照片。
我在拍的时候有人问是哪里的,我只好说是铁路局的,因为也没有别的办法。有时他们盯我,说别拍了,我就收起相机。走了一段他们看我没动静,就不跟我了,这时我又拍了。从1月8日开始,直到4月5日,这期间我去了许多次。可能是这批拍照的人里面去的次数最多的一个。尤其是3月以后,几乎天天去。
这幅《团结起来到明天》是在4月5日上午10点左右拍的。头天晚上广场上的花圈都被收走了,人们愤怒了,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高唱国际歌,从大会堂开始手挽手地走,目标是广场东侧的“工人民兵指挥部”,那是一个小楼,如今已经没有了。那景象十分悲壮,颇有走向刑场的气概。我赶到他们的前面拍了几张,自己也很感动。这一天是整个活动的高潮,对周总理的爱,对“批邓”的不满,对“四人帮”的愤怒,全都在这一天里爆发了。
我也很奇怪,那天我下午4点就回家了,我住崇文门附近,先把卷冲了,然后又去了广场。这些底片现在还存着,当时家里人很支持,嘱咐我藏好,我就放在一个高中同学家里,还有一部分在我母亲的医务室里一个空药瓶里,她是工厂里的医生。我的“藏品”里还有一段3分钟的电影呢。那是高强借给我的电影机,还有罗小韵和北影的李晨声给我的电影胶片。可惜我想拍的时候没有电影机,那时一般人不敢借给你呀,谁都怕出事。高强的电影机是自己买的旧货,在那个年代就算不错的了。结果我拍了3分钟那机器就出毛病了,没法拍了。要不然我有足足一小时的胶片呢。这3分钟的片子后来在新影厂的纪录片里用了,我还是那个纪录片的特约编辑。
吴鹏:端着相机的“四五英雄”(2)
在天安门拍照的人不少,这可以在后来吴鹏主编的大型画册《人民的悼念》中看到,但论精品,还是要数这几个人的作品。提到“四五”作品,就要提到这本画册,还有一个叫《人民总理人民爱,人民总理爱人民》的大型摄影展览。而吴鹏就是这其中的骨干分子。有了这样的形式,作品才有可能传播得更广、更久。
整个画册的文字是我写的,而且这本画册已经开始有了“专题”的思路了。以往的画册大都是单张作品,没有“专题”这样一个概念。编辑的过程也是一个漫长的时期,到最后只有我一个人在坚持,其他人都有各自的工作,而且也只有我能知道哪个照片是谁拍的。1978年一年我都在编这本书。
说到这本书,无论是摄影界还是新闻界抑或是中国历史界都不应忘记它。这本书在当时就印了10万册之多,而且以后没有再版,它与《天安门革命诗抄》、《革命诗抄》等构成了“四五运动”的最为直接、最为真挚的图文纪录。“四五英雄”们的确为历史作出了贡献,而作为这本画册主编者吴鹏,他无疑也是英雄榜上的人物。
从1976年底到1977年2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6位老师以童怀周为笔名,相继编辑了革命诗抄两本,同时七机部502所和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的几位同志也编辑了一本革命诗抄,在当时广泛传播,影响很大。我们知道,那是需要很大的胆识和勇气的。我和高强经常在一起,就谈论着要是出一本摄影画册,也会像诗抄那样感人的。1976年10月,罗小韵和高强分别带着自动化所和二外的同志们来我家找我,说要出书,借调我来当编辑。策划人是自动化所的王安时、王樵裕。其他成员还有罗小韵、李晓斌、高强、王志平、任世民、安政等。我们在任世民家碰了个头,就算是成立了编辑组。到1978年1月,我们就到北京科技局照相室高强的暗房里上班,那时只有他是“专业”的。第一天的工作就是征集照片。我和王志平是编辑组长,罗小韵管征稿退稿,李晓斌管联系作者,高强和我制作彩色照片,小韵、晓斌做黑白照片,我们通过各自的摄影圈子开始了工作。一个月之后,我们的“后援单位”扩大为五家: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革命诗抄》编辑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童怀周,七机部502所《革命诗抄》编辑组,《世界文学》编辑部《心碑》编辑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图书资料室。这些人是《革命诗抄》的编辑者,所以说,这本画册也是革命诗抄的延续。
实际上,比这早的时候,王志平就自己编了一本名叫《国丧》的影集,收集了四五百张“四五”照片,在朋友之中、社会上流传,影响很大。吴鹏自己也放了100多张照片制成影集通过熟人送给邓颖超。李晓斌也用这种办法送到邓小平家。鲍乃镛也制作了影集送到了邓颖超家、华国锋家和新华社。所有这些都表明这一批青年人是多么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心中的思念,并渴望得到某种支持。
当时同在天安门拍摄、后来成为该画册编辑之一的李晓斌回忆说:
编画册的工作没白天黑夜,没有报酬,吃饭自理,骑自行车满北京跑。将近一年后,上学的上学,调动的调动,只有我和吴鹏在坚持,过了三周,我也调到了中央实验话剧院,只剩下吴鹏一个人了。他兢兢业业地干到###平反、画册出版。平心而论,无论从编辑画册的责任心和编辑思路,还是“四五”期间拍摄作品的数量质量而言(画册中用了吴鹏的150张,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我认为吴鹏是“四五”摄影人中的杰出代表。尤其是4月5日那天,冲击大会堂、烧小楼、烧小车、手挽手喊口号、广场上的血迹等等,吴鹏都拍了。而我那天也在现场,相机就在军挎包里,很多该拍的我没拍,也不敢拍。我身边的一个日本记者先是胶卷被曝光,相机被扔上天摔得粉碎,人又被打得满脸是血,最后我们历史博物馆的人们把他保护了起来,让日本大使馆来接走。编画册时,吴鹏提议:同类片择优,尽量多用其他人的,少用编辑组的,大家非常赞成。吴鹏那时只是一个工人,能有这样的胆识,真让我佩服。
能有这样的胸怀着实难得。实际上,吴鹏拍摄的作品本该采用更多、获奖更多。最初,在五个一等奖中,几乎都是吴鹏的,但他只同意上了一个。
吴鹏说:
那时征集的底片可能有上万张。且大多数没有样片。我们只好全部放大,大概用了四五十盒相纸。我们的原则是:同一内容的135底片让位给120底片;编辑组成员的让位给其他人。1978年搞了一年,我一直在印刷厂盯着,1979年1月正式发行。编的时候事情还没平反,我们认定这事早晚会平反。等到快印刷了,1978年11月14日,中央批准,###平反了。有5家出版社抢着要出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