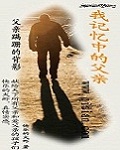烙刻:记忆中的影像-第1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摄影者来说,这时最重要的事就是怎样将胶卷保留下来。在广场上拍照的十来天中,我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被跟踪,况且周围的人都知道我去广场拍照,我的家人当时作为邓小平的“同党”正在挨批,家里是不安全的。于是迅速地将胶卷冲洗出来,仔细地用几层塑料袋包好,连夜把这些胶卷转移到一个朋友处,嘱咐说不管发生什么事,这些胶卷一定要保存好,它们会有重见天日那么一天的。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当时的很多报社的专业记者都不让去广场,只有个别大胆的人悄悄地去,所以当时的报纸上没有这方面的照片,而这恰恰给了业余摄影者们一个施展的空间,不经意间,历史便造就了一大批纪实摄影家。由于天安门在北京,首都的摄影者就占据了天时地利,如果没有这些摄影发烧者,那中国的摄影史重要的一页,定会留下极其遗憾的空白。尽管后来在编辑画册时,有很多专业记者也拿出了照片,但获得好评的传世作品几乎都是这些业余摄影爱好者拍的。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而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童怀周(笔名)编印了两本收录“###”诗词的《天安门革命诗抄》;与此同时,七机部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的几位同志也编印了一本《革命诗抄》。当时这几本诗抄在社会上反响很大,人们争相购买。在北京可以说每家都购有一两套书,至今我家中还保留了几套。
由此,我和一些“四五运动”的摄影者结识了。自动化所《革命诗抄》编辑组的王安时和王樵裕及二外的童怀周,大家私下议论,如能出一本“四五”摄影集那该多好呀。没想到王安时、王樵裕他们也就真的下了决心,积极筹备起这事。
1977年11月下旬,画册的第一次碰头会在任世民家中召开,参加会的有王安时、吴鹏、高强、李晓斌、王志平、任世民和我。会上决定由自动化所筹钱出画册,把我们几个人从各自单位借调出来,专门组成画册编辑组,我们几个人当时都是摄影爱好者,吴鹏是北京铁路局工人、王志平是农业出版社美术编辑、李晓斌是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工人、任世民是青海齿轮厂工人、我是北京新兴袜厂工人,只有高强在北京情报所从事摄影工作。虽然当时“###”没有平反,但我们几人所在单位都很支持这事,很快我们将手续办好,到高强所在的北京情报所照相室暗房上班了。后来安政也加入进来,编辑组成员由7人组成。
。 最好的txt下载网
谁是“四五英雄”?(3)
编画册第一件事就是要征集照片。我们几人当时都有自己的摄影圈子,通过这些朋友将编画册的消息传出去,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很快我们就征集到几千张底片。后来在《人民的悼念》画册中作者这一栏是这样署名的:“摄影及图片提供者”,共有120人之多。这里面有很多人不是照片的作者,有提供作者住处的,有来义务帮忙的。总之,当时这本画册还是地下出版物,因为“###”没有平反,既无经费,更无报酬,但没有一个人计较这些,画册的编辑工作非常有序地进行着。我当时在编辑组负责征稿退稿,并和晓斌负责制作黑白照片,吴鹏和高强制作彩色照片。当时编辑组7个成员每个人都拍有很多底片,加上征集来的,估计我们看到的有上万张底片。所有底片都没有样片,这样制作黑白照片的工作量就很大。据李晓斌回忆,黑白放大相纸就用了40至50盒,所放照片约在两三万张。当时大家干活没黑没白,共同的心愿就是要把画册编好。经过两三个月的时间,放大照片的工作基本完成,我也于1978年2月至3月间调到科学出版社任摄影记者,离开了编辑组。是吴鹏一直在编辑组坚持到了最后,排版打样,直到画册出版。1978年11月《人民的悼念》画册还在印刷厂打样,11月14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得以平反。这本“地下出版物”也由北京出版社正式出版;印数10万册,销售一空。
事后,我们这些人被称为“四五英雄”,大家都相继走上专业摄影岗位。20多年来,我从来也没有以“英雄”自居过,我想我们当时和广场上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一样,不过做了一件很本分的事情,今后再有这种事我们还会去做。“四五”的摄影者们当时是怀着一种社会责任感去记录那时发生的一切,以避免那段历史影像的空白,因为专业摄影记者都被禁止去天安门广场拍照,这种精神及社会责任感将伴随我们一生。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王立平:音乐家,摄影家(1)
提到中国摄影史就要提到王立平,就是那个著名作曲家王立平吗?他不但是作曲家,还是个著名摄影家。他的那幅名作跟他的那些美妙的歌曲一样著名,是中国摄影史上的传世之作。他还是那个著名的青年摄影团体—“四月影会”的发起人之一,而且连这个名字都是他起的。可能有些人不了解他在摄影方面的情况,那是因为他后来全力投入到音乐和政务方面,摄影界的事则较少过问了。
1999年,《中国摄影》杂志就读者喜欢的摄影作品作了次调查,结果在前10名中就有王立平的那幅名作《让我们的血流在一起》。这让他很开心,离开摄影界这么多年,广大的读者仍然没忘记他,没有忘记那个刻骨铭心的事件—1976年的“四五运动”。
“四五运动”在中国是个大事件,在摄影界也是大事件,不仅造就了许多纪实摄影家,同时也是许多职业摄影家至今难以启齿的事件—因为这一段时间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他们几乎都“封镜”了,没有去天安门广场,去了的也没敢拍几张,结果,数以百计的业余摄影者大显身手,在兴奋和恐慌中记录了中国历史上这重要的时刻。这些作品连同后来的文字记录以及当时的革命诗抄构成了那个时期最完整的纪录。
这张照片是在1976年4月4日上午拍的,实际上我在4月2日就去了。从2号到4号我连续去了3天,天天是阴天,加上当时的压抑气氛,那些日子真是沉闷。我在1973年时买了个苏联产的二手泽尼特单镜头反光相机,在那时也算不错的了。我一去就是一天,那时我住在东直门附近,骑车到天安门,中午就随便吃点东西。新影厂已经接到指示,不许去天安门,我那时正好要去海南岛出差,按惯例,出差前可以有3天的准备时间,我正好用了这3天。本来我定了3号的票,结果我又偷偷去把票退了。那时我已经34岁了,由于艺术圈子和知识分子中间经常议论,我已经知道了很多关于“四人帮”的事情,应该说对这些事已经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了。所以就知道###绝对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我既然有相机,有这个意识,那就不能错过。
那时我在新影厂工作,专职作曲。在新影厂里还有点“方便”—可以用点胶卷的片头。我到了天安门一看,人山人海。用一个词形容就是“群情激愤”。有人在念诗,有人在抄诗,有人在哭。我那时已经练就了一套功夫,就是想拍什么时,先在一边调好距离、光圈和速度,然后突然举起相机按一张,马上又跟没事似的眼睛转向别处,俨然一副老练的样子。因为那时有两怕:一是别人怕你,怕你是便衣,将来拿着照片去抓人;二是我也怕被便衣盯上,将来抓了去问,你拍照片干嘛。我想那时好多人都有这种恐惧心理。
由于形势紧张,我只能自己去,不敢叫伴儿。后来我听说,新影厂的一些老摄影师还是在总理追悼会上拍了一些会场外的镜头,比如广场上的人们,现在看起来很珍贵。后来我们发现,在广场上拍摄的几个人都很相似:背着黄书包,不吭声,闷着头拍……像鲍乃镛(在四五运动中拍了许多珍贵照片,其中一幅《白花献给周爷爷》获一等奖)、吴鹏、李晓斌,等等。我总共拍了68张,其中有8张不能用,只有60张还可以。在后来纪念总理的展览中和《人民的悼念》画册中以及新影厂出的纪录片中,我的照片一共被用了30张,使用率“高达”百分之五十!但是另一个数字更让人惊讶:在为悼念总理准备的展览过程中征集到了两万多张底片。而这已经是经过了有关部门查找、收集,大量胶卷被放在照相馆里不敢去取,以及自己怕事而亲手毁掉了底片等等几道“劫难”之后的事。
现在看到的这幅照片我拍了3张,而其他画面只拍了一张。因为这时人们的情绪很高涨,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个人身上了。画面中的那个人叫王海力,是个铁路工人,他用手指的血写了:“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将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您!”人们看了都很感动,纷纷和他握手表示敬意,大家一起高呼:我们支持你!我们愿意跟你一块流血!那情景真是感人。我后来的标题就是从这句话来的。广场很平,没有高角度,我就举着相机,往后仰了一点,还稍微拍得广一点,以保证画面完整。那个人已经被人们抬了起来,坐在人们的肩膀上,这才显得他很高。这样“盲拍”的照片还可以,我挺高兴。我用的是国产代代红21定黑白片,光圈是,速度1/100秒。
4月4日拍了以后我回去休息了一会,晚上又出来了。到了天安门一看,人少多了,满广场都是便衣—他们都穿军大衣,很容易看出来。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就没打手电,也不敢锁车子,干脆就推着车吧。这样边看边走,到了12点,开始有紧张的脚步声,有人收花圈了。我看见有人在念诗,当时就有几个人给按在地上了。我就赶快跑,但东西北三个方向都被封了,我只能往南边跑。围封的人群里也有好人,告诉我们说:快走吧!就这样我从包围圈里逃了出来,赶回家就冲胶卷。而那天晚上的花圈都被收走了,第二天是4月5号,人们发现花圈没了,才有“还我花圈”的愤怒,导致情绪进一步激化,这就是“四五运动”。
后来听说,4月4日晚清场时有不少人被抓,也有人自行车锁了,被按车号追踪抓去,我们算幸运的。我冲了胶卷后就交给我妈妈了,她又缝在我的小外甥的旧棉裤里,一直到“四人帮”被打倒之后才拿出来。
。。
王立平:音乐家,摄影家(2)
由“四五运动”引起“四月影会”,由“四月影会”引起一大批中青年摄影家的崛起,这在摄影界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准备悼念周总理的展览和编辑《人民的悼念》这本画册的过程中,这批青年摄影家已经显露出他们的才华和敏感。在1979年4月他们的作品首次展览时,则标志着他们的群体力量开始形成。这个群体对当时的传统力量是个巨大的冲击。整个过程中,王立平一直是重要的参与者,而且很有“老大哥”的味道。因为在对外公关、协调各方关系的过程中,青年摄影家们难免有过激的想法,而王立平的策略是柔和委婉,把对立的状态降到最低程度。现在看来王立平确有他的过人之处。
从广场拍回来之后我就冲卷,当时没敢放大,因为风声很紧。我们厂里有很多废胶片,那时大家爱做镜框,我就找了些废胶片故意剪成有片头那样的半圆状,卷回暗盒里,如果有人查,就说已经曝光了。这一切都做好之后,我就出差去海南了,为了逃避,我故意在海南呆了很长时间,大概有一个半月。去海南的火车上我就听说###是“反革命事件”,心中暗暗庆幸我拍到了历史的一瞬间了。我出来前跟家人说,绝对不能交出来,那样会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会按照片去抓人。
我从海南采风回来之后,我们的支部书记肖远问我,你去了广场没有?去了。你拍照了没有?拍了。被别人发现没有?应该没有。那你就咬定没去。就这样,我又被保护了。我们厂的老导演于村曾经在拍摄时帮助过我,我的母亲也冒着风险替我藏胶卷,所有这些,说明成功的荣誉不应该记在我个人的账上。
我的这些照片首次发表就是在悼念总理的展览和画册上,那次用了我的18张,后来新影的纪录片上用了24张,总共获得了400元稿费,在当时这也将近是一笔巨款了,但是我一直不敢自己用,因为这个钱来得不易,是有人流血流泪的情况下,是人民大众的民心所向的体现之下,我们只不过赶巧纪录下来而已。所以这笔钱我几乎都用在了四月影会的活动当中了,比如给大家买点汽水、包子,买点展览用的绳子之类,王志平(“四月影会”的###之一)比我付出的还多。
这些底片的下落是个问题。在编辑《人民的悼念》这本画册时,底片都交了,后来新华社也复制了一部分底片给我们,现在我手里只有这张原底了,因为就这一张拍了3张。其他的不知去向了,有的也是几经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