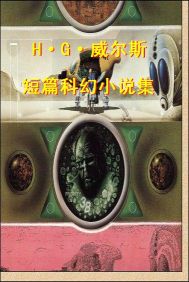外国中短篇科幻小说1000篇 (第四辑)-第13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哇!”葛拉底叫道,她是鲍森医生的护士,她刚刚到这儿。“这么多好的东西而且又没人管。我最喜欢这些紫水晶。”
“别碰它们,”鲍森医生说。
“哇,头儿,”葛拉底没有礼貌地说。“你看看这个壁橱!
裘皮的衣服!真丝的衣服!看看这些鞋子!多可惜啊。“
“她要是醒来就不可惜了。”
“她是精神分裂吗?”葛拉底问道。
“不是,她得了一种沉睡病。
——晕睡性脑炎。那时她才二十岁。“
“我不知道在纽约还有舌蝇。”
“不是那种晕睡症,葛拉底,你到过哪儿啊?”
“我知道所有的事情,”护士说。“它是一种病毒,在大流感时期到处传播。十年中,五百万人得了这种病。然后,就停止了。从那以后,就再没有传播蔓延过。”
“真是谢天谢地。她母亲在1925年1 月1 日早晨发现她站在卧室的镜子前,从此后她就昏迷不醒。
“天哪,”葛拉底说,并颇为同情地看着萨利。“也就是说,已七十岁了。可这不可能呀。她看上去没过30岁呢。”
鲍森医生又仔细地端详了一下萨利。他知道她的真实年龄,所以他可以把她想象成七十岁的老人,但葛拉底说的没错。她的皮肤像年轻人一样光滑没有皱纹,也许是因为她没有受过炉火的熏烤、怀孕的苦痛、感情的冲击之由吧。她的头发像少年人的一样惊人的柔软。她紧闭的双眼已经历了五十年的蹉跎岁月。
鲍森医生浑身一阵颤栗。很久以前,在一处涨潮的潭水里,他发现了一种复杂的生物,边缘是波浪状。蓝、黄、粉相间煞是可爱,他俯下身去将其从水中捞出,打算仔细端量一下。在他的手中,它破裂了,所有的漂亮色彩碎成了粘液,沾满了他的手指。
当然了,萨利可并不是池中的生物。他现在终于承认尽管她年事已高,但她确是一个美丽绝顶的女人。他轻轻地抬起她的下巴,开始端详她平静而毫无表情的面孔。“明天我们就开始采用维他命和锻炼疗法,”他说。
以后的每天早晨鲍森医生都会为萨利注射维他命。接下来,葛拉底喂给她婴儿食品,并为她擦去从口中溢出的食物。
每当食物滑入她的食道,萨利都会自动把它们咽下去。但有时她会被噎住。每当此时,葛拉底就向前扶起她的身于,好让食物流出来。
“真是难以想象会有人五十年如一日地干这种活,”葛拉底道,边嘟哝边费力地把萨利扶起让她坐直。
“要帮忙吗?”鲍森医生正坐在桌后钻研一期医学杂志。
“她不很重,”葛拉底说,擦拭着萨利流到下巴上的马铃薯泥。“这看起来是没希望的事儿。”
“这就是我们来这儿要搞清楚的。”
“她的手臂和腿看起来好些了。”葛拉底抬起了萨利的手臂并用手指弹着。手臂上的肉迅速地弹回了原状,不像原来葛拉底手指的印痕要几秒钟才能消褪那样。她弯曲了一下萨利的手指并分别弯曲着她的每个手指。令人奇怪的是萨利的手指总有种抵制的力量。当葛拉底停止时,手掌又恢复成鹰爪状。
早饭后,护士做完了一天中众多锻炼例行工作中的第一项。她轮番抬起萨利的腿,并把她的脚前后弯曲。她用力地按摩着她的下巴并把萨利的手臂伸展过其头顶。“这也许对她没什么好处,但我相信情况会好的,”葛拉底说道。
“她看上去恢复得很好,”鲍森医生说。他走到床前。萨利躺在床单上,像一个蜡人。而葛拉底一下子坐在椅子上,筋疲力尽,气喘吁吁。
萨利原来矮胖的身子在葛拉底的照顾下有了反应。她胸部变得挺拔了,她的腰部呈现出柔美的曲线。那在二十年代算不上合乎时尚也说不上妖娆的身躯,看来真有些妖媚。鲍森医生迫使自己移开了目光。
“我得把她打扮得漂亮些,”葛拉底说道:“她的妹妹今天要来。”
当萨利的妹妹见到她时,她哭道:“她看起来这么年轻,像个小姑娘。”她用一条手帕擦了擦眼睛。“我记得她原来的样子,充满活力。她做了所有我不敢去做的事儿。自从我丈夫死后,她就是我的一切。”她拿出了一把木梳子开始梳理萨利的头发。老妇人长满老年斑的手抚摸着萨利卷曲的孩子般的头发。两个女人看上去甚至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的萨利睡着了,”老妇人边哼着边摆弄着连衣裙。萨利躺在床上像一个价钱昂贵的玩具,她的眼睛瞪着,熟视无睹。“我的小公主会醒来吗?”她的妹妹吸着鼻子,擦着眼睛。
鲍森医生没有回答,因为他不知道萨利是否正常地睡着。
她在想什么?她知道周围正发生的事儿吗?萨克医生的一些病人说他们清楚任何事情但不能做出反应。一个人怎能在这种状态下生存下来而不完全发疯呢?
当他小的时候,她的母亲给他讲过有关活死人的传说。
“这个活死人幸福吗?”他问母亲。“他喜欢这样活着吗?”
她笑了,“他谈不上幸福不幸福,他没有灵魂。”
“一个没有灵魂的东西怎么能活着呢?”
她朝外望着暗淡的华沙市的轮廓。在阳光的粉色余辉里一队飞机嗡嗡飞过。“那碰巧了,”她道。
究竟什么才能在萨利身上起作用呢?
他开始试用左旋多巴。什么都没发生。每天注射药物并急切等看结果。没有任何结果。
也许是刚开始的问题,或是要达到她血液度水准的问题。
他谨慎地加了剂量,还是没有结果。
然而他感到有什么事发生了。当他第一次走进房间时,它像一个博物馆,但是现在它有点,真的,有点像一个年轻女人的卧室。一盒滑石粉敞着盖子放在梳妆台上,盒子的边上轻轻地溢出了一些,好像有人刚刚把手指放进过一样。一个乳白色的镜子面朝下放在床边的桌子上。当他用手指抚摸它时,它几乎还有点儿余温。一件质地极薄的睡衣斜搭在椅子上,它的花边在玫瑰园吹来的微风中飘动着。
鲍森医生把萨利从床上搬到椅子上。他抬起她时,一种意料之外的情感支配着他。很难形容这种情感。他做这种活已很多次了,而她不过和卷起的地毯一样不令人感兴趣,但是这一次她给人的感觉——有些不一样。她软软的胸部抵着他的衣服,她的呼吸搅动着他脖子边的毛发。他迅速地把她放下,在她周围放了一些枕头以便她不致于倒下。
“你在哪里?”他问萨利,她交叉着双手,目视前方。接下来他又看见;她的双手,不再像海豹鳍状肢那样向里弯曲。
它们重叠着放在腿上。仿佛她正有礼貌地等着有人来请她跳舞。
“葛拉底!”鲍森医生喊道。
“喔,唷,”葛拉底说道,走上前来,用手抓住萨利的手。
她的手松松柔软地放着。“喔,天哪,我从没想到会发生什么。
她也许会真的醒来。“
“你认为我们一直在为什么工作?”
“那太可怕了。我的意思是,她二十岁时就睡着了。她的父母都死了,她的房子没有了,她所有的男朋友都成了老头儿。她能拥有哪一种生活呢?”
“她现在拥有的是哪一种生活呢?”鲍森医生说道。
“没有人知道,是吗?”葛拉底道。“她醒来照镜子时会发生什么事儿呢?人们真想不到她睡着时她只有二十岁。”葛拉底忙乱地整理原本已很整洁的房间。她从玻璃花瓶里拿出了褪色的丁香花,走出去要换成玫瑰花。她回来时,把乳白色背部的镜子放在梳妆台底部,一些毛衣下面。
“我更喜欢她手僵硬的时候,”美容师再次来的时候说。
“你得努力去修剪她的软指甲。”
鲍森医生不屑于回答。他看着她给萨利洗头发。当美容师涂上香皂进行清洗时,葛拉底不得不将萨利的头放在盆子上去。当水流到鼻子时,这个老妇人轻轻地发出嘟哝的声音。
“你小心点儿,”葛拉底说。
“做了这么多次了,她从来没有抱怨过,”美容师从她的盒子中拿出一个吹风机。“她有一头漂亮的头发。使你很想在上面做些发式。一次我给她做了一个埃佛罗发式,但是她妹妹让我给它改掉。”
当美容师给她染睫毛时,老妇人眨了眨眼睛。“你看见没有?她从前从来没眨过眼睛。”
“别把睫毛液弄到她眼睛里,”葛拉底说。
在梳妆台的一个抽屉里有一个摆满香水瓶的架子。“我每次都用一种不同的香水。真是好东西。”美容师给萨利和她自己都喷上了阿尔佩芝牌香水。“你要点儿吗?”葛拉底选了乔伊牌香水,喷了起来。“一次我还试了皮衣和珠宝,但是给她妹妹抓住了,差一点丢掉这份儿工作。她妹妹每周都检查一遍。”
“我知道,”葛拉底叹了一口气。她把萨利推到窗前,挑剔地审视着她。她的头发乱蓬蓬地立着,眼眉用铅笔描过,使她的脸上有了表情。葛拉底给她穿上了连衣裙,在领口上别了一个银树叶的领针。
鲍森医生从后面走上来说,“她看上去真漂亮。”
萨利坐直了身子,向他咧开嘴笑着。“舞会在楼下,”她说道。
她伸出手来,走向镜子。这时,楼下的大钟以最惊人的方式敲着。这正像留声唱机要停下来时那样。音调变低,歌词听不见了,直到你分辨不出它们。她喜欢和莉莉。旁兹一起唱那首意大利街歌。莉莉。旁兹有高昂音质美的嗓子,当她唱“啦啦啦”时,唱机就会停下来,听上去像井里的一只青蛙,莎利把它叫做“莉莉。旁兹”,母亲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
钟的响声似乎慢了下来,直到不比外面刮着的风声大多少。时不时地风好像停了,一会儿又开始吹了。
萨利看着镜中的男人,现在她看出他和她父亲一样大的年纪。奇怪的是以前她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风又开始吹了——很难讲,刮了多长时间。但这并不要紧。站着还是很舒服的。她感到很轻松,她的头也不痛了。“我醉得很厉害,”她笑着说。现在风又在吹了。但它现在更强劲了直到她注意到这是钟在敲,是新年的钟声。
“有人弄坏了唱机,”她傻笑着。钟又敲了,很正常地,最后一响。突然房间里充满了光亮。太奇怪了。她一定是整个晚上都呆在这儿了。他迷惑地看着她。
“舞会在楼下,”萨利说道。
“上帝啊,”在她右边有一个声音说。萨利转过身来,看见一个黑人穿着护士的制服。在她旁边是一个非常异乎寻常的人物。她有一头红铜色的头发,显然不是天生的,而且像刷子一样直立着。穿着一件可怕的破烂衬衣和男式的裤子。萨利听说过这样的女人,但是真正见到一个时还是很吃惊。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站在她前面的男人说。
“当然,”萨利说。“我长着耳朵,不是吗?天哪,是早晨了。我猜我晕倒在地上了。好了,警官,你抓住我了。是我吃了那片面包。”她无助地伸出了双手。
“她听上去十分正常,”那个黑人用一种惊异的口气说道。
“萨克医生描述过类似的病例——突然间地清醒,好像大脑里有个开关装置似的。”那个男人伸出手来抓住萨利的手。
她突然感到很害羞。他不像那些同她摸弄的男孩;他同父亲一样大。她把手抽了回来。“你是一名医生,是吗?我猜妈妈以为我病了,但是我只不过是喝醉了。请保证不要告诉别人。好吧,”她站起来,两手交叉握着。“多么美的玫瑰,是给我的吗?”她那双明亮的眼睛望着医生。
他伸出手来扶住她。“你得小心会儿!”
“显然得小心点儿,”萨利说,从下眼睑看着他。她让他扶着她坐下。“怎么回事,这不是我的房间。有我的东西,但这小很多。我知道!我被送到医院来了。”
“你一直都病着,”医生开始说道。
“这该死的汤姆给了我什么东西。哼,我希望他娶一个老母猪。好吧,我的确觉得不好受,但是不要言败,小伙子们?”
她滑稽地转了转眼睛。“又一个灌多了酒的牺牲品。喂,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你们都瞪着我?”
“我想我得走了,”那个有着刷子一样红头发的女同性恋者说。她拿起一个小的白色手提箱,一句话也没说就逃掉了。
“你们两个呢?脱下手套呆一会儿。”
萨利快速地说着,掩饰她那种拘束感。好多的事情都不太对头。透过窗帘她可以看到一个玫瑰盛开的花园,而她知道那是冬天。医生的鞋子看上去那么古怪,谁又听说过黑人护士呢?
护士服也很古怪——一太短太紧了。还有很多的小东西:电灯开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