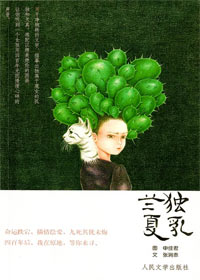独乳兰夏-第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小心,野兔可有劲儿了。”
兰夏刚把它抱到膝盖上,兔子就飞奔窜入麦田。
这兔子跑得也太快了点吧,原来它蓄谋已久啊。
但反而是兰夏摆出一副发怒的神色。“我送给你的灰羊毛手套呢?”
“我没戴。”
“不合适吗?”
“不合适。”
“天气凉了。”
“天没冷到要戴手套的地步啊。”
“我可以再送你一副。”
“再?你不是已经给我了吗。不要再说手套的事情了,简直就像恶癖了。”Noel厌烦地说。接下来你我都知道他是想遮掩一件马上就遮不住的事情。
他把话说完,兰夏就把那对从猪骨里拉出来的手套掏出来给他看。
“我从垃圾堆里找出来的。你为什么要丢掉?”
“我没丢……”Noel也很诧异,不像是撒谎。
“那为什么会在垃圾堆里?”
“我送给法蒂玛了。”Noel只好这样说。他确实说了实话,他是个相当老实的人。
兰夏迅速站起来,疾步走回屋子。
。。
是老妇
撞开二楼书房的门,兰夏走到法蒂玛背后。
法蒂玛惊愕地回过头,兰夏按停她手上的钩针,把灰色羊毛手套扔到法蒂玛两腿中间:“你为什么要把它们丢掉?”
看到手套,法蒂玛一下就变得手脚慌乱,简直是乱甩般地站起来。
“我戴男人的手套不合适,所以我就扔了!”她抓住兰夏的裙子,双膝一软,直接坠落到地上跪下了,眼睛涌出泪水。
“求求您,求求您兰夏小姐,不要告诉泰勒夫人!”
“这理由的不充分。”
法蒂玛把脸埋到兰夏的一双膝盖之间一直哭,“求求你,别告诉泰勒夫人……”
“我不会跟泰勒夫人说的。为什么你想的是不让泰勒夫人知道而不是恳求我的原谅?”
“这……”
“我原谅你了。你走吧。”
法蒂玛还没起来,兰夏就已离去。
兰夏对你说,在法蒂玛面前,我自觉老妇。法蒂玛泪汪汪的眼睛和垂坠的棕色蓬蓬头,抬头看的神情,完全一副劫后余生,从雪崩中逃出生天的可怜兮兮的少女的样子。一个已经活了三百年的少女和十几岁的生理正常少女站在一起,多少会自卑的。
法蒂玛对你说,夺走自己身边人的妒忌还包括为何兰夏竟能有少女容颜,却仿佛年长50岁,有她没有的不动产。一旦弱势出现,卑微凸显,自己的娇弱又战胜了她。用卑微来换取的,是自己的高兴。
兰夏知道她在挑衅,明明知道底细也不能制服,走到结论处是对自己的不能制服。她仍然无法不去注意法蒂玛手上的瘀肿,愤怒之中忽略不掉的好奇。
可你仍旧不解的一点是,Noel把手套送给法蒂玛的事实以及背后情感走向到底如何,竟被兰夏忽视了,或被兰夏忘记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送信 炸弹
你看到起了风,台阶前的风很大。你只能从泰勒夫人的哭泣中感觉风量的大小,因为面前的麦浪已经没有了。她的泪痕贴入肌肤的纹理,水分蒸发得一干二净。
收割后的麦田是光秃秃的黄土,茬短的麦根又使得田野扬不起什么灰尘。天越来越冷,远方低压的黑云是马上要下雪的象形判断物。你突然萌发了憎恨,因为寒冷甚至连空气都夺走了,使你无感并且有恨终归无可奈何,它让你体验到它并且仅仅能够感觉到它单独一个。
泰勒夫人就这样注视着远方,仿佛陷入悲伤思绪并因此失去理性,就好比受冻的你。
但法蒂玛一从屋子里走出来,泰勒夫人又懂得把手上的信递给她。
法蒂玛接过信,奔进田地里,冷风让她裹紧外套。有一辆车在远远的地方等她。
在车里,兰夏等待法蒂玛跑过来。空间的局促和寒冷以及两个人的隔阂融合在一起,车门关了以后,温差让玻璃起雾了,那俩人除了呼吸就只是呼吸了。
你启动了汽车,你是司机,你穿的是军服。你从后视镜里观望你的乘客。
直到你把汽车颠到麦田中间,车轮子上下被泥块磕绊着,她们两个人不得不产生身体接触,才开始说话。法蒂玛先开的口。
“我不敢把这封信送给那个人。我连邮局都没有去过。”你从后视镜里扫了她一眼。
法蒂玛不停捏手里的信。她没有擦玻璃上的雾,却也望窗外风景,看那堆虚掉的绿团黄团向后漂。突然一圈顶圆的红菇冉冉莽莽,轻飘飘浮起来,接着轰隆空空的震动传到耳边,又续着一条挤压过的小弦音绕过头扯到远处。
你很镇定,说了声:“飞机走了”便恢复先前时速。法蒂玛被激得浑身毛孔都张开,缩躲到前座下面。明知是空投的榴弹落在临近村野,却一副恨不得炸在身边的表情。
“你觉得这封信有用吗?他真的能让他们把Noel放回来,不用回军队吗?”
兰夏还没有回答,紧接着法蒂玛又追问道:“你希望他死吗?”
兰夏想了想道,“你觉得呢。”
末了兰夏又说,“他根本不可能会死。”
“为什么?”
“你不必知道。”
。 想看书来
守蛋的母鸡
广播里播报英军和德军的战事。Noel收拾物品,他比兰夏早走一天。
“不要走,不要走”,泰勒夫人像一只守蛋的母鸡在守她的蛋,围Noel不停转,怕有人来抢了他,杀了他,吃了他,却不敢阻拦Noel本人。
“兰夏还欠一周课,是不是兰夏?教完再走……”兰夏根本就没有在现场。
“没关系,她可以比我晚一天。汽车也是明天才来,我坐火车去。”
母亲没有借口了。可怜她还不死心,将过去要把箱中衣服拉出来扔掉的地步。
“你还在休假,编理由吧!”
“军人怎能不参战?”Noel声音不重,听得也很义愤填膺。
后来泰勒妇人果然去抢他箱子里的衣服,把一件白衬衣扯出来。Noel干脆不要那件衬衣,箱子用力一抱,走上楼去。
泰勒妇人没有继续扑上去,相反她抹掉眼泪,呼出两口长气,接着就去打电话。
“我要给约瑟夫打电话,让他给你求情,他认识你们军队的人——”
Noel箱子一扔就从楼梯上跑下来阻拦她:“少做些开不了口的事!”
法蒂玛在厨房扶门看。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失败的信
远远的,狐狸似的人影从黄田里走回来了。
法蒂玛裹紧大衣,吸溜着鼻涕,仿佛偷食不堪之物。
信还在握她手里。她把信用还回去的感觉递给站在门口等候的泰勒夫人。
“我不敢去找那个人——”话还没说完,泰勒妇人重重一掌把她括到门柱底。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医生
跟随Noel和兰夏,坐汽车,坐马车,坐火车,步行,经过两天时间,现在你在一间军用医院的手术室里面。
医生灭去明火,借用几把镊子的协助,把那颗牙齿从类似陶瓷烤炙台的地方夹起,丢进一个装有透明液体的宽口瓶子中。牙齿发灰,并不洁白。
在气泡的震荡翻滚中,你能从牙齿根部看到一团莹滟滟的光珠,这边翻一番,那边剌一刺,是一颗微型胶囊的尾部,活如废水沟中洒欢寻食的小鱼在太阳底下闪耀的白肚皮。现在它正在经历的是液化钙的凝固过程。
你眼前的医生是半个秃子,他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因为所戴的单眼罩放大镜的缘故,他的小眼睛呈现出更浮肿的状态,几乎把眼睛都挤没了。
兰夏躺在牙科手术椅上。医生把牙齿夹过来了。
“你平时吃东西是习惯用左边牙齿还是右边牙齿?”
“左边。”
“那我把它装在右边,这样对你日常生活不会造成威胁。”
“这叫氰化钾是吗?”
医生惊疑地顿了一会才道:“是叫氰化钾。那是麻醉药而已。”
“别担心,不用对我撒谎。我已经知道了,如果这颗胶囊在水井里破裂,打个比方,那喝这口井的全村的人都会死掉。”
医生立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你放到我嘴里,让我感觉一下。”
医生呆滞服从兰夏的指示,把牙齿丢进她口中,像丢一颗方糖浸入他未曾尝过的咖啡,东南亚口味。
好喝嘛?那颗肥肿的牙齿在兰夏口腔中周旋。
突然兰夏露出奇怪笑容,整个人仿佛瞬间顽皮起来,对医生说:“我现在咬咬试试看?”
医生吓坏了,接连说不不不,不要开玩笑!
兰夏说,我在逗你玩。
。。
护士
接下来护士们给兰夏扎针。一个护士使劲抱着她的脑袋,将她的脖子折出最大化的扭曲,耳朵已经贴到肩膀了。她抱得这么紧是为了让兰夏不能移动。
如果你站到手术椅的另外一侧,你能望见兰夏的脖子暴露出青虬的静脉。第二名护士过来用手指压住她的血管,让筋脉更劲爆。但给兰夏打针的那个小姑娘无法将麻醉针头刺入兰夏的皮肤,那针头几乎都弯折了,也插不进去。
“医生,您是不是更有力气一点……”发话的护士显然自己都不相信是因为女性的柔弱无力,才导致针头无法刺入皮肤的状况产生。
医生接过护士手上的针,他当然也是扎不进去的。医生没辙了,只好敲兰夏的脖子,探测一下是不是里面铸了钢板,很滑稽地。接触到的当然是皮肤的柔软。
眼见三名护士和一个医生都束手无策,兰夏就拍拍抱着自己脑袋的护士的手,示意她放手,然后坐起来揉揉脖子道:“我的手指很柔软。打针可以打这里。”
兰夏对他们伸出自己的手,尖锐的拇指指甲抵着中指,掐深了,中指随时都能被刺破,流出血来的模样。
医生道:“但不需要刺这里啊。麻醉区域是口腔附近。”
“那你们直接动手术吧,不用麻醉了。”
。。
手术结束
医生推开门出来的时候,他的手套已经除下来,白大褂搭在手上。
门外的沙发上靠着一个人,他已经睡着。除了这间手术室,走廊的左右两边都没有亮灯,已经没有别人走动。时间已过深夜。
医生将睡熟的Noel推醒:“结束了。”
Noel费劲地睁开眼皮。“没有什么意外吧?”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但她几乎一滴血都没有流。而且不用麻醉。”
Noel鼾睡半闭的眼睛挤出一丝笑容:“她是有点特别。”
“您已经把氰化钾的事告诉她了吗?我还以为她不知道,你不怕,她……?”
“不是已经成功了吗?”,Noel说了这样一句话。头一低,又继续睡了。
医生担忧又怜悯地望向门内。
兰夏的背景,正在披风衣,像进来做牙科例行检查的女子。
医生害怕跟走出来的兰夏打照面,在她没有出来之前就快步躲入漆黑走廊。
Noel已经预支她的性命去做赌注,她不是千年前就死掉的湖泊和化石。
虽然她顺从他的意见,想和氰化钾挑战。玩乐的表现,是她的异样和反常。
你听到我的言论,我说,一个女人倒贴回去保护一个男人就是这样的结果,女人变得受虐。以为代他受苦就是快乐的事,强迫地让自己受虐。更因为愈加觉得她是他的保姆,第二母亲。插不进皮肤,不可感知的恶伦之念,明明渗进她的血。
但你不一定这么想。你离我的距离更远,你与她更近。在你心中,她是一座圣洁的雕像。作为雕像,她替你抗争时间也替你争取永恒,她须以雕像之身代表雕像之体背后的附加想象而忘记自己。她以为那就是她自己,她以为她可以变成你。
但她不能变成你,你也不是她的家属。她以为的她的追求,不能如她所愿,被当成任何不被束缚的可以发光的东西。我不觉得一颗沙子被贝壳的唾沫裹了裹,就可以叫珠宝了。真正的钻石只有太阳一个。爱情、背叛、自由、渴望,纷纷独立于这个你这个我这个她,但不可能被重合。所以她的所为即将被印证为徒劳。
她幼年起即背负着寿命只得别人三分之一的诅咒,最后也只是,跟医生开个小小的玩笑,就过去了,却搞得医生比她本人还要悲伤。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玩蛇的印度人 去伦敦
你我进到火车内部。
车厢里,兰夏和Noel正在用膳,他们处在单独的厢房里头。
Noel正给自己倒酒的时候,一股笛音穿肠过肚地捅进来了。
印度人推开他们的门。笛子是他吹的,他走得真快。他对兰夏和Noel挤眉弄眼地吹了一会。
Noel漠然放慢用餐的速度,兴致寥寥,同时也不好意思开口驱他出去。后面车厢的老太太打开门,探头过来看。印度人看到多了一个观众,就更加卖力吹。接下来他把背后的竹篓放在吃饭的桌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