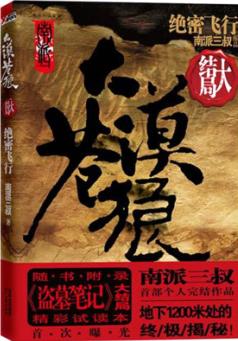飞行员--勇敢的真实故事-第5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但据她的侄子拉尔夫·塞兹对我讲,“在华伦·厄尔死后,埃维就不再正常了。”埃塞赖恩·古德纳说:“她性格变了,变得非常低落,寡言少语,她还做过一段理疗。”比利·温德尔回忆说:“那么多年中,埃维总是企图自杀。她的第二个丈夫也和她离了婚。”拉尔夫·塞兹还说:“她的精神有些崩溃了。她一时心血来潮就嫁给了第三个丈夫,可她甚至都不认识那家伙,婚姻只持续了一个月。”后来的大部分时间埃维都是在小型医院里度过,并于1991年死在医院,享年87岁。哥伦布·卢埃林是在她出殡时给她护棺的人之一,在她的最后几年,哥伦布常去看望她。“她从未跟我提及过她的儿子被杀害的细节,”哥伦布告诉我。但她说在儿子死后,她已经不在乎她是活着或是死了。在她临死的那天,心情不错,但事实上她已是肝肠寸断。
也有的日本人痛不欲生。当池谷叶侣年轻的女儿跑过田野时,恰巧遇上一名美国飞行员的轰炸,被炸死了。“我女儿那时年仅16岁,”池谷说,“那是一个痛苦的结局。我从我的内心深处憎恨、厌恶那个敌人。我只想沿着那一击的轨迹找到杀死我女儿的那名飞行员,把他干掉。”
3月10日,当舟人和代和她的家人一起逃离燃烧弹引起的大火的时候,她还是个小孩子。混乱中,她和父亲两人与母亲分开了,当时母亲的背上正背着她的小弟弟。早上和代和父亲回到了家,但家已变成了一堆灰烬。他们在那里等着母亲的归来。过了一会儿,他们发现妈妈已经在那儿了;只是他们没认出来。母亲正坐在地上,盖着一块军毯,衣服已经被烧成了炭,头发也被烧焦了。
和代问她的弟弟怎么样了,“旭子怎么样了?”
母亲只是沉默。当她不语时和代仔细地看着母亲。“我看到当时她背着旭子,”和代说。“在旭子的腿与母亲的身体贴近的地方,有严重的烧伤。她的胳膊肘被烧得露出了嫩肉,很有可能是在大火中为了保护旭子造成的。她几乎不能走路。”
在东京这次大火的袭击中,和代的母亲失去了她的两个孩子——旭子和广子。火焰把旭子从她的背上夺走了。
“我过去常常带母亲去他们的坟前祭祀,”和代说道。“她总是一边向坟墓上泼水一边说:‘广子,你一定很热吧;旭子,你一定很热吧。’”
人们总是倾向于将战争的另一方所表现出的残暴看成是其内在的文化的一种表现,而往往将自己表现出的残暴说成是正当的、被迫进行的反抗行为。在我的行程中,我感到在一些美国人中,对日本人在二次大战中的所作所为有一种隐约积聚的怨恨。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感觉却在那些没有参加过二次大战的年轻一代美国人中最强烈。根据我的经验,在太平洋两岸的退伍老兵已经和解。听听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的话我们就不难做出这种判断。就像曾两次驾飞机对广岛和长崎进行原子弹轰炸的雷·加拉格尔所说的,“当你没有真正处于战争中时,你只能做出二流的猜测。你必须亲身经历那些年代,走过那段路才行。”
如果世上有人有恨的权利的话,这个人一定是格伦·贝里。他经历了巴丹死亡之旅(许多战俘头被砍掉,尸首扔得遍地都是),曾被装在两艘该死的破船里(被闷在华氏130度高温的船舱里,人们简直全疯了),在福冈战俘集中营里成为医学试验的对象(“那三个月里我不记得任何事情”)。他告诉我,“那是一种思想灌输,他们的士兵被灌输了这样的思想:天皇是太阳女神的后代,没有必要去尊重人类的生命,哪怕是他们自己的。”
“我已经原谅日本人了,我还有日本朋友。我尊重日本人,是因为他们已经改变了原来的态度,这一点我已经搞清楚了。我相信,任何一种文化都可以被按照领导人的意志塑造成任何形式。”
年轻时作为一个日本士兵曾给中国带来过灾难的人,NB23F本杉木同意格伦的观点。现在中国人民欢迎他到中国去,因为他会如实地讲述日本的过去。当我坐在NB23F本君郊区的家里品着茶的时候,他告诉我:
是这种天皇体制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人们认为为天皇他们可以做任何事。士兵们随时准备效忠天皇,为天皇贡献一切。他们认为,在中国他们可以做任何事。其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都是源于这种天皇体制,其他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归根结底应由天皇来承担责任。我当然对天皇心存怨恨。
我想将我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公之于众。我们必须将军国主义思想从这个世上彻底根除。
飞行员奥斯卡·朗险些丧命于“大船”战俘营。回来后姐姐看到他消瘦的身形哭了,她极度藐视日本人的这种行为。但是奥斯卡向她解释说:“这些日本士兵只不过是在按命令行事,同我按命令行事没什么区别。我扔下的炸弹杀死了好多人,可这是我的工作,而他们所做的也正是他们的工作。”
新加坡人伊丽莎白·舒瓦是残暴的日本酷刑的受害者。战后她认为那些对她施以酷刑的人不应被处决:“都是这罪恶的战争。如果不是战争,他们也有自己的家,就像你和我一样。就像普通人一样,他们有家人、父亲、母亲、妻子和孩子,还有他们的工作。是战争使他们变得如此残暴、毫无人性,因此我说我原谅他们。”
在进行调查、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经常让人感到迷失了方向。起初,我觉得我知道什么是正义,但在我听了日本人以及美国人所讲述的故事后,我竟变得很茫然。
我认识当时的一些飞行员,就是他们扔的炸弹促成了这场可怕的战争的结束。我在东京和已经81岁高龄的桥本良子一起度过了一天,她曾经跳入冰冷的河水中救她的孩子。在整个采访过程我们将一盒纸巾来回的推来推去,讲完后,我问她感觉美国人怎么样。
桥本良子说道:“一名军队教官告诉我,如果你只杀了一个人,那就是谋杀;可如果你杀了很多人,你就是英雄。我想那些在东京杀了很多日本人的美国人在美国应被奉为英雄吧。但同时我们日本人也在中国杀人,那时日本把杀戮当作是一种巨大的成就来表扬。我们都做了坏事,战争就是这样。”
在2001年夏天去日本的一趟旅行过程中,我在横滨和76岁的玉村文夫度过了一天。他是旧金山日本移民的后裔,就是他曾伴随着吉米·戴伊走向了死亡。一枚标有“扶轮国际”的饰针在他的大衣领口闪烁,“你知道,日本是二号扶轮社国家,”玉村自豪地说。
我们从上午一直谈到了下午,直到下午三点钟才结束。长途的飞行使我感到非常的疲惫,四点钟我挂起了房间里的窗帘以遮挡阳光,躺下来睡了一会儿。
一阵电话铃声吵醒了我,时钟显示我只睡了40分钟。是玉村,他问我是否愿意和一位前日本帝国海军上士聊一聊。内田有纪曾在巢鸭战俘监狱服过七年刑,因为他当初按吉井大尉的命令处死了吉米·戴伊。
“我回家后,刚才和内田有纪通了电话,”玉村君说。“我叫他和你谈一谈,他有些犹豫。内田有纪说:‘不,我不想同任何人谈关于那个时代的事,即使同我的孩子都没谈过。'”
玉村继续说:“但我告诉他无论如何都要和你谈一谈。”
在我黑暗的旅馆房间里,我问玉村君:“内田有纪应当有将近80岁了,因此他的孩子们都在四五十岁左右,是吧?你为什么认为他一定会同我谈呢?你知道,他甚至同他的孩子们都没谈过这事。”
玉村君说道:“我告诉他你的父亲曾在硫黄岛服过役,你为人是很公正的。刚才我对他讲:‘不管有没有你的参与,布拉德利都会写这段故事的。内田有纪,现在正是你谈自己看法的时候。'”
第二天一早,我搭上了一辆火车。盯着窗外急速逝去的乡村风景,我在想:同一个56年前残忍地砍掉了吉米·戴伊的头颅的人碰面会是什么样子呢?
内田有纪君为人态度温和,略显保守地穿着蓝色的西装、白色的衬衫,打着红色的领带。他向我提起了我的父亲,以期使我认识到,那些并非出于自愿而杀人的人内心非常痛苦。我不停地对他说:“你必须服从吉井的命令……你不觉得被判入狱七年太多了吗?”不,他回答道,他认为对他的判决是公正的。日本战败了,他本以为会死掉。“美国人对我很好,”他明确地告诉我。
谈话的最后我说道:“内田有纪君,当然,我想你肯定已经意识到我将会写一些连你的孩子们还不知道的事实。”
“我打算在我死前告诉他们,”内田有纪说道,他的眼睛有些湿润。“或许他们会从你那里找到答案,请写一本好书。”
从日本回来后,我给吉米当年的飞行员战友打了电话,告诉他们有关吉米遭遇的更多的事。乔·博恩曾看到吉米在父岛跳伞逃生,他是个心直口快、坦率认真的人。一天当我正在同他谈话的时候,他给我讲述了太平洋两岸的相互仇恨以及他是如何的轰炸那些无助的日本士兵以及平民。“事情就是这样,”他给我解释道。我在想,如果我告诉他我曾遇到了一个曾向他的朋友举起屠刀的日本人,那他会做何反应。
我向他解释内田有纪是如何在上级严格命令的胁迫下出于无奈执行了命令。内田是一个顺从的雷达技术员,当那个醉酒的上司强迫他举起他那从未使用过的军刀时,他内心里对美国人根本就没有一丝仇恨。很多的日本少年都受到了这种“伪武士道”狂热精神的残害,内田有纪也是其中之一。那些酗酒吃人的军官们胡乱调遣他们军队的行为并不是日本武士道传统的一部分。
在我向博恩讲述了有关吉米在弥留之际的遭遇后,电话的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That'sahellofathing;”他说道。
过了几秒钟我问道:“什么是ahellofthing?”
“嗯……我觉得他们把吉米的头砍掉是不对的,”他回答道。
现在该轮到我沉默了。我同意博恩的观点,但就在几天前在我听内田有纪君讲那段历史的时候还掉了眼泪。我试探着说了一句:“是的,但或许你炸死的那些平民也是ahellofathing吧?”
接下来是更长的一段沉默。
我不知道我是否说得太多了。
最后,博恩叹了口气说道:“是的,我想这只是取决于你站在哪一边。”
乔治·布什同以前的敌人实现了和解。在其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作为商人、驻联合国大使,以及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代表,他同日本人进行了许多友好的交往。1989年,因为参加裕仁天皇的葬礼,布什总统经历了严重的政治危机。1991年12月7日,在夏威夷珍珠港举行的纪念仪式上,他站在美国和日本退伍老兵的面前宣布:“说心里话,我对以前的敌人不怀有任何怨恨。”
2002年,老飞行员博恩已经是78岁高龄了。对于过去经历的那些战火、爆炸、流血以及恶魔,他大多保持沉默。但在梦里,他是否看到了一个小岛,在那里年轻无助的他担心自己会死去呢?他失去的那两位战友怎样了呢?我曾听到他说:“我一直在想着他们。”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叫我把他带回到过去那个时代,当他还只是个20岁的小伙子,作为一名飞行员处于极大困境中,直到这时我才知道他有多么的想他们。
2002年6月17日,那是一个周二,我站在硫黄岛的柏油碎石路面上,欢迎前总统布什的飞机到来。我向前总统问候道:“欢迎您到硫黄岛来,总统先生。”
我们走在黑色的沙滩上,然后爬上了折钵山。“这就是美军战士们当年升旗的地方,”我说道。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是另一位曾在这片圣地上走过的总统。
2002年6月18日,硫黄岛的黎明时刻,我们醒了。太阳女神就是在这里用她的第一缕阳光照耀了日本。她首先将温暖带给了硫黄岛,然后又将光芒撒向无人居住的一个个小岛直到日本大陆。只有在这时,这块升起太阳的土地才将光芒撒向世界的其他地方。
那个早上的迟些时候,日本飞行员们用直升机将我们带到了父岛。飞机着陆时,我努力地从兴奋的人群中寻找我以前访问中结识的一位朋友。我发现他还是那样英俊、健康,皮肤被晒得黝黑,我向他招手,示意他到直升机降落的附近来。
他就是埃布尔·萨沃里。纳撒尼尔·萨沃里,父岛的开拓者,他曾在1853年迎接了佩里准将。现在,149年过去了,纳撒尼尔的玄孙又有幸这样做了。埃布尔·萨沃里微笑地说道:“欢迎您到父岛来,总统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