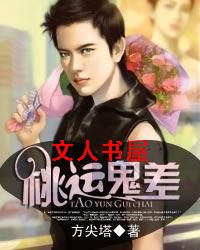鬼差-第2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屋中最显眼处,挂着两幅画卷,诸多人在画前围观。画中的一个人我很熟悉,他的眉目唇齿,是我从小看到大的,最终长得逸群绝伦。
一旁挂着的女子画像,却是我不识得的。
“怎么苏大夫和苏小妹长得如此迥异?”画前站着的女子问她的丫鬟。
“小姐,城里很多人都这么说,可能苏小妹是苏大夫收留的义妹吧。以苏大夫的慈善心肠,也未尝不可。”
“为何本朝就无如此俊逸的大夫呐?”
一干人等一同点头。
原来这画中的女子居然是我,想起曾跟苏毓描述过的:
苏毓……我眼睛不大……单眼皮……鼻梁有点塌……嘴唇不厚……但也不薄……我不漂亮……在人群中也不显眼……喜欢穿青色衣衫……白色的鞋……头发总是长过肩膀就剪了……剩下的扎成马尾……
世人五官平凡的都是差不多,他画不出个所以然来,难怪我怎么瞧着都不像,只是那眼中的寂寞倒是画了个十成十。他也不知何为马尾,头发只作冲天冠,煞是奇怪,看上去真像个小女孩,难怪旁人把我当成他收养的。
有个女子想伸手碰苏毓的画卷,回春堂的伙计赶忙上前阻止,“小姐,这画像已挂了两百多年,日出挂起,日落收起,才保存完好,请远观切勿碰触。”
那女子讪讪地收回手,羞红了脸。
“若您想要苏大夫的画像,出门左转街尾有位师傅临摹了许多,可供购买。”
“谁说我家小姐要苏大夫的画了,小姐冰清玉洁,长于书画,只是想看看这画功如何罢了。”丫鬟大声回护主子。
伙计答得也不亢不卑,“此画是苏大夫真迹,他当年曾学画两年,最后只是画了这两幅流传后世,便已惊艳画坛,几代下来画家临摹收藏无数。再者,买苏大夫画像者,多半也是为了家宅平安。”
学画两年?他倒是把自己的俊俏貌美画了个十成十的,而我的画像挂在旁边,虽觉得是个陌生人,但在他心中,恐怕就是我本人了。
这就是苏毓眼中的我,而这画卷就挂在他旁边,不知陪伴了多少年月。
××××
两百多年不见,紫禁城扩建得更加巍峨壮观,苏毓曾住过的太医院四合院早就不知去向,是拆了还是改建,抑或是炮火毁灭,无从揣测。
我在离开京师两百多年后又回到了这里,京师对我而言,若没有苏毓,只是一个驿站,休憩后便前行……
鬼差在人世间穿梭,阅尽沧桑,直到一日,连自己都变得无感无欲后,悄然离去。这是鬼头大哥告诉我的,一个决定去投胎的鬼差跟他说的话,看似是离活人距离最近的工作,却是最被漠视,在冷眼旁观几多年后心终究结冰。
现今想想,死魂又何尝不是?自那日起,阿八便消失了。
本以为苏毓的墓必在凤阳城边,但我转了一圈,却一无所获,幸而在酒楼中听人提起,才知道苏毓的墓在京师。
为什么会在京师?
一般官员即便是在天子脚下当再大的官,最后也是荣葬故里祖坟。苏毓祖籍不知是在哪里,但肯定不在京师,那年他当院判,是第一次入京城。
不知我回去后在京师又发生了何事,但京师中若真有对于现在的我最值得纪念的地方只有一个。
我踏上一节节石阶,山路早已被铺平多时,石阶因为踩踏过多而光滑润泽,即便如此,走这山路的人还是甚众,携着香烛,心怀虔诚,如同百年前的我和苏毓。
月老庙前划归出一大块空地,红砖墙琉璃瓦围起,前朝皇帝御赐的颂碑立于门口,门中却只是起了个简单的坟冢。
苏毓墓。
××××
你葬在这里吗?我抚上石碑。
很难想像我手下的,是苏毓的墓碑,我走时,他还是翩翩少年。
墓碑上的颂文我看不懂,是长篇古文,只是那卒日我看得分明,他应是死于三十九岁。
三十九岁,尚且风华正茂。
三十九岁,我还能在他身边十四年。
绕了一圈,除了墓碑上简单的生卒时辰外,就无其他线索。
我走出门时才发现门口的颂碑背面居然刻有字,而且甚是简单。
“月老庙,跪垫下。”
这是苏毓留下的线索?
月老庙的庙楼被几度翻新,再加建二楼,可见香火鼎盛确实很有帮助。
我走入时,唯一一个简单的跪垫旁居然还有文人墨客,揣测留在颂碑背面的谜题。
“跪垫下明明无任何字,为何在苏毓墓那里却指明内有玄机?”
“非也非也,月老庙不定指这间。天下月老庙何其多,苏毓不过是故弄玄虚。”
“难不成要一家家去找?”
“何人有如此闲工夫。”
“听闻明朝也有痴情女子踏遍天下月老庙,只为找到苏毓真义。”
“结果如何?”
“谁人知道。”
这群不知是求姻缘还是闲啃牙的书生调侃了半天,才随着香客离去,偌大的庙竟然没留有半个尼姑或和尚打理。
我摸了摸香案,一日下来,居然还是纤尘不染,是用法术的吧,蹲下把跪垫移开,下面的确是平坦石板,没有一丝痕迹,但若能在这庙中任意使用法术,想必这石板上的,也只是雕虫小技。
暗运法术恢复石板先前的样子,我手下变得凹凸不平,密密麻麻,细细摸索后,我倒抽一口凉气。
“摸到了?”背后阿八的声音响起,略带撒娇,“这局我都布了两百多年了,现在你才来,真等煞我了。”
生前死后的声音会有所不同,我记住了,这苏毓死后的声音。
“其实不止这跪垫下,整个庙的地上都是,你再摸摸。”声音渐渐冷却,尖锐。
我转过身唤他,“苏毓。”
苏毓依旧是那绝魅容颜,可眼角却不再带有一丝和煦。
那地上遍布的只有一个字:恨。
“你等了两百多年,竟是想告诉我,你恨我?”
灰飞烟灭
“恨啊……”
苏毓蹲下身的同时,地上的刻痕均浮现,绵延至整个庙堂之内。不是法术布上的,是一笔一划刻的。
我垂首看着他,“苏毓,五年后我回去,你二十五岁后到底发生了何事?为什么?”
他只是坐下,靠在庙门上,望着这偌大的庙堂。
“原来几百年来,我曾刻过那么多恨字。”他纤长的手指抚过一个个刻痕,“刻时在想什么呢?大概在臆想当你发现时的震惊和一旁看着的我的快意吧。”
我跌坐在跪垫上,重复问着,“为什么?我不懂。”
“七七,记得我生前最后跟你说的话吗?”
你定要回来,我会等你,五年……十年……我都会等你的。
“能让我如此恨你,只有一个原因:你不曾再回去过。”
我惊愕地看着他。
“苏毓二十五岁,在回春堂隔间摆上了一桌酒菜,等了一宿,一天,一月。”他说起时好似在说别人,无关痛痒的平淡。
“苏毓三十岁,酿出了新酒,等了几宿,病倒。”声调转为沉闷。
“苏毓三十五岁,”他扯开嘲讽的笑容,苦涩极了。“他居然还在等你。”
他手一挥,垫旁的字便变了,微微泛着蓝光。“这跪垫下本不是‘恨’。”
“五年了……我等你。苏毓。
“十年了……我等你。苏毓。
“十五年了……我在等你。苏毓。
“我将去做一个赌注,若是还未见到你,那只能缘尽今生。等你的苏毓。”
他站起身走至我面前,托起我的脸颊,眼角露出丝丝危险,“知道苏毓是怎么死的吗?”
我摇头。
“苏毓在三十七岁时学了画画,画出自己二十五岁的容颜,他怕再等下去,即便你回来也会嫌他年华逝去,老态龙钟。”他冷哼,“真是傻子。”
“三十九岁那年,发生了什么事?”我直觉刻痕中提到的那赌注必定很危险。
“那年,南方一个城镇爆发鼠疫,官兵把守城门,禁止出入,且强出城门者杀无赦。”他扶起我垂于胸前的青丝,目光晦暗,“苏大夫济世救人,孤身入城。”
“为什么?那是鼠疫啊?”
“我怎会管这些,你真以为我有菩萨心肠?”他呢喃,“七七,你了解我的,我怎么会牺牲自己去就那些该死之人。”
“究竟是为什么?”有些了然,但我的心被楸紧,只能愣愣听着。
“当时我只是想着……那里死人那么多……没准你在那里做你的差事。”眼泪一滴一滴滴在我脸颊上,“或许我能找到你。”
“我……”明明只是离开五年,转眼却成百年。
“苏毓从来都没有入葬,即使有坟墓也是空坟。明朝皇帝不管城中百姓死活,一道圣旨下令烧城,他连尸身都没留下,灰飞烟灭。”
庙堂中静默下来,直至我脸上泪迹已干。
苏毓放开我的脸,靠着我坐下。
“这两百多年来,我日日找寻着,只为找到你问个缘由。”他自顾自言说,“刚遇见你时,尚且旁敲侧击,想套出点什么,没想到……你只是从明朝到了清朝,至于为何没回去,连你自己都不知道。”
“七七,我一直等在这里,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这石板上的字迹是我抹去的,‘恨’也是我刻上的,除了这字,我已找不到其他文字来显得我不那么卑微。”
“曾几何时几乎以为是个梦,你没有容貌,没有名字,那我在记挂着谁?记挂着哪副容颜?”
“七七,五年后是何原因已无从查究。我只想问一句,当日在此地的诀别,是不得已为之,还是你的抉择?”
两百年前的离开?
我想起二十岁的苏毓当日落寞地跪在神像前,我是瞧了他修长身影最后一眼才转头的,我没有履行和阎王的赌注,是我自己选择的清朝。
我艰涩开口,“苏毓,对不起,是我自己选的。”
即便有那万分之一的机会,我却并没有去赌,随意抛下了他。
肩旁的他走了,我独自坐着,想象两百多年前苏毓在此的绝望祈求。
人世间总是这样的,当爱不爱时,在付出与收回间徘徊,踏出一脚,是希望与对方更进一步,若没感觉到对方的靠近,却埋怨起自己走的太冒失,于是又缩回一脚,并不是每一次后退都能重新出发的。
我这一步的后退,竟将苏毓逼至面前,生生付出了两百多年光阴。
命途多舛
庙宇高堂之中,青阶石板之上,我席地而坐了一整夜。
生前从不曾欠人人情,更不曾亏欠过别人,我自认是老好人一个,被欺压是常有的事,偶尔忍气吞声便过去了,但如今愧对的竟是苏毓,让我心酸无措。
鬼差再无知无觉,这心毕竟还是有痛感的,痛得想落泪,却落不下来。不愿用法术释放泪水,那……让我觉得自己虚伪可悲。
莫不是前世的寂寞,我也不至于一步步接近苏毓;莫不是想引得他心中的一席之地,我也不会无端端透露医术于他;莫不是想让他记着我,别忘了我,又何必在此对他许下那五年十年之约?
鬼差的外表下,我终究残存着人的心,自私、贪慕。
××××
“七七,七七……”小倩使劲摇着我。
“怎么了?”我有些茫然,回过神才发现自己正在饿死酒楼。
饿死?原来一切就是从此开始纠结的。
小倩看着我的眼神有怜悯,有担忧,居然不久就凝结成泪,滴滴落下。“七七,我知道你不想哭,看你这失魂落魄的样子。不要这样,我代你哭,好不好?”
全地府都知道我让苏毓等了两百多年吗?
一旁又伸来一只手将我拉过,是鬼头大哥。
“七七?鬼差聂七七?”他也叫唤我。
“怎么了?”我出声,依旧带有哭腔。
“啪。”鬼头大哥一个耳刮子甩过来,痛是不痛,但对他这行为,我震惊多于疼痛。
“死老吴,你干什么?”小倩忙拉开他。
“听说有鬼差因为刺激过深而得抑郁症,最后只能喝孟婆汤去投胎,我想甩个巴掌让她清醒清醒,反正又不痛的。”他还振振有词。
“你白痴啊,有这样清醒的吗?都说不痛了。”小倩也很勇猛地甩了他一个耳刮子。“最多是转个脖子,你说能清醒吗?”
好吧,若他们是想把我从自怨自艾中拉出来,那他们已经成功了一半。
“你们到底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
甩得正凶的小倩和鬼头大哥定格停下,齐问,“你还不知道?”
我摇头。
鬼头大哥扯出夸张的笑容,堪比当初骗我当鬼差时的灿烂笑容,“没事,没事。哪有什么事啊?快回你的清朝去,那大小阿哥还等着你定魂呐?”
我皱眉看了看他,转向小倩,“告诉我,什么事?”
小倩傻笑,“你刚才哭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