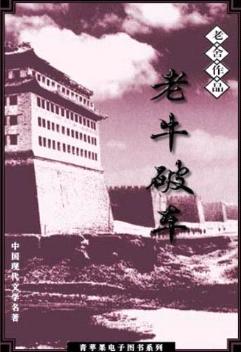老牛破车-第1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趣味。因灵感而设计,重人或重事,必先决定,以免忽此忽彼。中心既定,若以人物为主,须知人物之所思所作均由个人身世而决定;反之,以事实为主,须注意人心在事实下如何反应。前者使事实由人心辐射出,后者使事实压迫着个人。若是,故事才会是心灵与事实的循环运动。事实是死的,没有人在里面不会有生气。最怕事实层出不穷,而全无联络,没有中心。一些零乱的事实不能成为小说。
大概我们平常看事,总以为它们是平面的,看过去就算了,此乃读新闻纸的习惯与态度。欲作个小说家,须把事实看成有宽广厚的东西,如律师之辩护,要把犯人在作案时的一切情感与刺激都引为免罪或减罪的证据。一点风一点雨也是与人物有关系的,即使此风此雨不足帮助事实的发展,亦至少对人物的心感有关。事实无所谓好坏,我们应拿它作人格的试金石。没有事情,人格不能显明;说一人勇敢,须在放炸弹时试试他。抓住人物与事实相关的那点趣味与意义,即见人生的哲理。在平凡的事中看出意义,是最要紧的。把事实只当作事实看,那么见了妓女便只见了争风吃醋,或虚情假义,如蝴蝶鸳鸯派作品中所报告者。由妓女的虚情假义而看到社会的罪恶,便深进了一层;妓女的狡猾应由整个社会负责任,这便有了些意义。事实的新奇要在其次,第一须看出个中的深义。
我们若能这样看事实并找事实,就不怕事实不集中,因为我们已捉到事实的真义,自然会去合适的裁剪或补充。我们也不怕事实虚空了,因为这些事实有人在其中。不集中与空虚是两大弊病,必须避免。
小说,我们要记住了,是感情的纪录,不是事实的重述。我们应先看出事实中的真意义,这是我们所要传达的思想;而后,把在此意义下的人与事都赋与一些感情,使事实成为爱,恶,仇恨,等等的结果或引导物;小说中的思想是要带着感情说出的。“快乐”,巴尔扎克说,“是没有历史的,‘他们很快乐’一语是爱情小说的收结。”
在古代与中古的故事里,对于感情的表现是比较微弱的,设若Henry James (亨利·詹姆斯)的作品而放在古人们手里,也许只用“过了十年”一语便都包括了;他的作品总是在特别的一点感情下看一些小事实,不厌其细琐与平凡,只要写出由某件事所激起的感情如何。康拉德的小说中有许多新奇的事实,但是他决不为新奇而表现它们,他是要述说由事实所引起的感情,所以那些事实不止新奇,也使人感到亲切有趣。小说,十之八九,是到了后半便松懈了。为什么?多半是因为事实已不能再是感情的刺激与产物。一旦失去这个,故事便失去活跃的力量,而露出勉强堆砌的痕迹来。一下笔时不十分用力,以便有余力贯彻全体,不过是消极的办法;设若始终拿事实为感情起落的刺激物,便不怕有松懈的毛病了。康拉德之所以能忽前忽后的述说,就是因为他先决定好了所要传达的感情为何,故事的秩序虽颠倒杂陈亦不显着混乱了。
所谓事实发展的关键,逗宕与顶点者,便是感情的冲突、波浪与结束。这是个自然的步骤。假若我们没有深厚的感情,而空泛的逗宕,适足以惹人讨厌,如八股文之起承转合然。Arlo Bates(阿洛·贝茨)说:“我不相信小说构成的死规则。工作的方法必随个人的性情而异。我自己的办法据我看是最逻辑的,可是我知道这是每一写家自决的问题。以我自己说,我以为小说的大体有定好的必要,而且在未动手之前就知道结局是更要紧的。”
这段话使我们放胆去运用事实。实事是事实,是死的,怎样运用它是我们自己的事。Arnold Bent(阿诺尔特·贝内特)在巴黎的一个饭馆里,看见一老妇,她的举止非常的可笑。他就设想她曾经有过美好的青春,由少艾而肥老,其间经过许多细小的不停的变化。于是他便决定写那《老妇们的故事》。但这本书当开始动笔的时候,主角可已不是那个老妇,因为她太老了,不足以惹起同情。杜思妥益夫斯基的《罪与罚》是根据他自己的经验,但把故事放在都市里,因为都市生活的不安与犯罪空气的浓厚,更适宜于此题旨的表现。这样看,我们得到事实是随时的事,我们用什么事实是判断了许多事实之后的结果。真人真事不过是个起点,是个跳板。我们不仗着事实本身的好坏,而是仗着我们怎样去判断事实。这就是说,小说一开首的某件事实,已经是我们判断过的;在小说中,大家所见到的是事实的逐渐的发展,其实在作者心中,小说中的第一件事与第末一件事同样是预先决定好了的。自然,谁也不会把一部小说的每一段都预先想好,只等动笔一写,象填表格似的,不会。写出来才是作品,想得怎样高明不算一回事。但是,我们确能在写第一件事的时候,已经预备好末一件事,而且并不很难,因为即使我们不准知道那件是什么事,我们总会知道那是件什么样的事——我们所要传达的与激起的情绪是什么便替我们决定,替我们判断,所需要的是什么事。明乎此,在下笔的时候便能准确;我们要的是“怒”,便不会上手就去打哈哈。及至写完了,想改正,我们也知道了怎去改正——加强我们所要激起的感情,删削那阻碍或破坏此种情绪的激发的。
由事实中求得意义,予以解释,而后把此意义与解释在情绪的激动下写出来;这样,我们才敢以事实为生材料,不论是极平凡的,还是极惊奇的,都有经过锻炼的必要。我们最怕教事实给管束住:看见或听见一件奇事,我们想这必是好材料,而愿把它写出来。这有两个危险,第一是写了一堆东西,而毫无意义;第二是只顾了写事而忘记了去创造人。反之,我们知道材料是需要我们去锻炼炮制的,我们才敢大胆的自由的去运用它们,使它们成为我们手中的东西。小说中的事实所以能使人感到艺术的味道就是因为每一事实所给的效果与感力都是整个作品所要给的效果与感力的一部分,仿佛每一件事都是完全由作者调动好了的,什么事在他手下都能活动起来。硬插入一段事实,不管它本身是多么有趣,必定妨碍全体的整美。平匀是最不易作到的。要平匀,我们必须依着所要激动的情绪制造出一种空气,把一切材料都包围起来。我们所要的是“怒”,那么便可以利用声音、光线、味道,种种去包围那些材料,使它们都在这种声音、光线、味道中有了活力,有了作用,有了感力。这样,我们才能使作品各部分平匀的供给刺激,全体象一气呵成的,在最后达到“怒”的高潮。所谓小说中的逗宕便是在物质上为逻辑的排列,在精神上是情绪的盘旋回荡。小说是些图画,都用感情联串起来。图画的鲜明或暗淡,或一明一暗,都凭所要激起的情感而决定。千峰万壑,色彩各异,有明有暗,有远有近,有高有低,但是在秋天,它们便都有秋的景色,连花草也是秋花秋草。小说的事实如千峰万壑,其中主要的感情便是季节的景色。
但是,我们千万莫取巧,去用小巧的手段引起虚浮的感情。电影片中每每用雷声闪光引起恐怖,可是我们并不受多少感动,而有时反觉得可笑可厌。暗示是个好方法,它能调剂写法,使不至处处都是强烈的描画,通体只有色而无影。它也能使描写显着细腻,比直接述说还更有力。一个小孩,当故意恐吓人的时候,也会想到一种比直陈事实更有力的方法——不说出什么事,而给一点暗示。他不说屋中有鬼,而说有两只红眼睛。小说中的暗示,给人一些希冀,使人动心。说屋中有些血迹,比直说那里杀了人更多些声势;说某人的衣服上有油污,比直说他不干净强。暗示既使人希冀,又使人与作者共同去猜想,分担了些故事发展的预测。但是这不可用得过火了,虚张声势而使读者受骗是不应该的。
谈幽默
“幽默”这个字在字典上有十来个不同的定义。还是把字典放下,让咱们随便谈吧。据我看,它首要的是一种心态。我们知道,有许多人是神经过敏的,每每以过度的感情看事,而不肯容人。这样人假若是文艺作家,他的作品中必含着强烈的刺激性,或牢骚,或伤感;他老看别人不顺眼,而愿使大家都随着他自己走,或是对自己的遭遇不满,而伤感的自怜。反之,幽默的人便不这样,他既不呼号叫骂,看别人都不是东西,也不顾影自怜,看自己如一活宝贝。他是由事事中看出可笑之点,而技巧的写出来。他自己看出人间的缺欠,也愿使别人看到。不但仅是看到,他还承认人类的缺欠;于是人人有可笑之处,他自己也非例外,再往大处一想,人寿百年,而企图无限,根本矛盾可笑。于是笑里带着同情,而幽默乃通于深奥。所以Thackeray(萨克莱)①说:“幽默的写家是要唤醒与指导你的爱心,怜悯,善意——你的恨恶不实在,假装,作伪——你的同情与弱者,穷者,被压迫者,不快乐者。”
Walpole(沃波尔)①说:“幽默者‘看’事,悲剧家‘觉’之。”这句话更能补证上面的一段。我们细心“看”事物,总可以发现些缺欠可笑之处;及至钉着坑儿去咂摸,便要悲观了。(奇*书*网。整*理*提*供)
我们应再进一步的问,除了上面这点说明,能不能再清楚一些的认识幽默呢?好吧,我们先拿出几个与它相近,而且往往与它相关的几个字,与它比一比,或者可以稍微使我们痛楚一点。反语(irony),讽刺(satire),机智(wit),滑稽剧(farce),奇趣(whimsicality),这几个字都和幽默有相当的关系。我们先说那个最难讲的——奇趣。这个字在应用上是很松泛的,无论什么样子的打趣与奇想都可以用这个字来表示,《西游记》的奇事,《镜花缘》中的冒险,《庄子》的寓言,都可以叫作奇趣。可是,在分析文艺品类的时候,往往以奇趣与幽默放在一处,如《现代小说的研究》的著者Marble(马布尔)便把Whimsicality and humour(奇趣和幽默)作为一类。这大概是因为奇趣的范围很广,为方便起见,就把幽默也加了进去。一般地说,幻想的作品——即使是别有目的——不能不利用幽默,以便使文字生动有趣;所以这二者——奇趣与幽默——就往往成了一家人。这个,简直不但不能帮忙我们看明何为幽默,反倒使我更糊涂了。不过,有一点可是很清楚:就是文字要生动有趣,必须利用幽默。在这里,我们没弄清幽默是什么,可是明白幽默很重要的一个效用。假若干燥,晦涩,无趣,是文艺的致命伤;幽默便有了很大的重要;这就是它之所以成为文艺的因素之一的缘故吧。
至于反语,便和幽默有些不同了;虽然它俩还是可以联合在一处的东西。反语是暗示出一种冲突。这就是说,一句中有两个相反的意思,所要说的真意却不在话内,而是暗示出来的。《史记》上载着这么回事:秦始皇要修个大园子,优旃对他说:“好哇,多多搜集飞禽走兽,等敌人从东方来的时候,就叫麋鹿去挡一阵,满好!”这个话,在表面上,是顺着始皇的意思说的。可是咱们和始皇都能听出其中的真意;不管咱们怎样吧,反正始皇就没再提造园的事。优旃的话便是反语。它比幽默要轻妙冷静一些。它也能引起我们的笑,可是得明白了它的真意以后才能笑。它在文艺中,特别是小品文中,是风格轻妙,引人微笑的助成者。据会古希腊语的说:这个字原意便是“说”,以别于“意”。因此,这个字还有个较实在的用处——在文艺中描写人生的矛盾与冲突,直以此字的含意用之人生上,而不只在文字上声东击西。在悲剧中,或小说中,聪明的人每每落在自己的陷阱里,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个,和与此相类的矛盾,普遍被称为Sophoclcanirony(索福克里斯的反语)。不过,这与幽默是没什么关系的。
现在说讽刺。讽刺必须幽默,但它比幽默厉害。它必须用极锐利的口吻说出来,给人一种极强烈的冷嘲;它不使我们痛快的笑,而是使我们淡淡的一笑,笑完因反省而面红过耳。讽刺家故意的使我们不同情于他所描写的人或事。在它的领域里,反语的应用似乎较多于幽默,因为反语也是冷静的。讽刺家的心态好似是看透了这个世界,而去极巧妙的攻击人类的短处,如《海外轩渠录》,如《镜花缘》中的一部分,都是这种心态的表现。幽默者的心是热的,讽刺家的心是冷的;因此,讽刺多是破坏的。马克·吐温(Mark Twain)可以被人形容作:“粗壮,心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