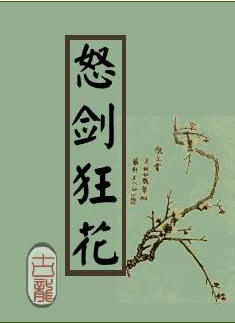狂花凋落-第6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出国执行任务的特工,向组织述职时间必须在抵达莫斯科后两个小时内立奇书…整理…提供下载刻进行,否则将视为违反纪律处理。傅索安踏进第六部那层楼面时,内卫问过姓名,让她去第五办公室。那里,已经有三名克格勃军官坐在那里等着她了,其中一个傅索安认识,是当初她从日本执行暗杀任务时主持述职的奥列格少校。见傅索安进门,三人站起来,—一跟她握手。奥列格少校指着其中一个穿西装的中年人向傅索安介绍说:“这是技术管理局的专家。”
傅索安听了,暗松一口气:看来,他们并没有抓住她的把柄,否则,技术管理局的专家就不会来了。专家来这里,是想当面了解“死亡老鼠”“死亡”的具体经过情况。奥列格少校仍是这次述职的主持者,他说了声“让我们开始吧”,他的助手马上按下了录音机的键钮,并准备记录。
傅索安已经有了述职的经验,便把自己登上“西伯利亚人”号货轮后一直到返回莫斯科的情况源源本本说了一遍。她在返回苏联的海上旅行途中,已经把述职内容反复考虑过,连什么环节用什么措词都已经准备好,所以说得很顺畅。尽管如此,也花费了大约两个小时。她说完后,奥列格少校点点头,微笑着说;“傅,你具有当一名作家的才能,叙述事情很流畅,思维相当清晰。作为述职主持者,我暂时没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要提问的。当然,按照程序,你还得写一份书面述职报告,在七十二小时内交出来。您有什么问题吗?专家同志。”
那个技术管理局的专家点点头,提了几个问题,都是关于“死亡老鼠”方面的,纯是技术问题。他听傅索安再次说明“死亡老鼠”的“死亡”原因后,不无感慨地摇着脑袋;“唉!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啊!”
傅索安说;“行动失利后,我想了想,应当是有办法解决这个难题的!”
“哦!”专家一愣,随即睁大眼睛盯着傅索安,“真是这样吗?你说说看!”
傅索安其实纯是即兴发挥,当下便借口开河:“我想可以给每套装置配上一个备用“老鼠”,一旦一个不幸‘老鼠死亡’,立刻换上另一个。因为通常说来,不可能接二连三发生这种意外事的。”
专家闻言大喜:“说得对!哎,我们这么多科学家聚在一起每次讨论没解决的问题,给你这么一点就基本上解决了!”他马上掏出笔记本,在上面记下了傅索安的建议。
口头述职进行到这里,算是暂告段落。接下去,是让傅索安写出书面述职报告,由审查人员比照录音和记录进行反复检查,技术管理局的专家也将对傅索安带回来的那个仪器进行检查鉴定,如果都没有疑问,那就不会再找她。反之,则需进行第二次、第三次甚至更多次数的口头述职,实际上也就是审查。
当然,傅索安被安排在对外谍报局第一招待所。她一进房间就往餐厅打电话让送来酒菜,独斟独饮,喝到六七分醉意,洗了个澡就睡觉了。次日,傅索安用了一整天时间写完了述职报告。述职报告送上去后,她闭门不出,静候结果。此时倒也心定,寻思事情反正已经如此,就只能听命运安排了。照她分析,这次述职应当是通得过的。
果然,十月革命节的前一天,傅索安接到通知:马上去对外谍报局第六部。傅索安赶到那里,奥列格少校向她宣布:述职报告已经通过。按照惯例,克格勃请傅索安吃了一顿饭,尽管未完成任务,但因不是她的责任,还是发了三千卢布的奖金。
傅索安打起了如意算盘:接下来最起码得让她休息一个星期,明天是十月革命节,红场要举行例行庆典,她叛逃来苏已经第六个年头了,一次也没观看过庆典实况,只在电视上见过。这次倒是个机会,可以去红场直接看看了。但是,这个算盘显得过于一厢情愿,酒还没喝几杯,在场的一位中校已经通知她了:根据人事管理局的通知,决定把她仍调回“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去工作。今天晚上立刻动身。
傅索安心里差点骂娘,但外表却声色不露,连连点头。她又一次感受到任人摆布的滋味,这和她一向桀骛不驯的禀性是格格不入的。
1973年11月9日,傅索安回到了“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
屈指算来,傅索安离开这所学校不过一年,但这里的变化却相当大。校舍扩大,还新开了几个科目,比如专门研究制造假人民币。
假粮票、假布票等票证的特别一班,专门负责制造假情报提供给外国情报机构的特别二班,等等。在这里接受训练的人数也已增加到一千八百余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从香港、台湾、澳门、越南、朝鲜、韩国、日本、蒙古以及苏联和中国接壤的加盟共和国招来的,傅索安意识到苏联方面已经越来越重视了对中国的谍报活动。
“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校长仍是布特卡少将,他在傅索安抵校报到的当天便予以召见,直接向傅索安谈了工作安排问题:学校已经设置了一个拥有四万册中国书籍的图书馆,可是直到现在也没有人专门负责,而是由俱乐部工作人员兼管着,这既不正规也管理不好,现在傅索安来,正好负责此事。布特卡最后说:“至于待遇,你仍和其他教官一样。凡是其他教官所享受的待遇比如薪饷数额、福利、年休假等等,你都同样享受。”
傅索安听了很是高兴,这样,她既不用和那些学员打交道,也和特务工作告别了,还能看大量中国书籍,真是求之不得之事,于是马上表态眼从安排。其实,傅索安应当想一想,克格勃为什么对她的工作作了这样的安排。克格勃所有的特务学校都有一个规定:不论学员还是教职员工,包括校长,只要调离一所学校了,就永远不会再让他回到这所学校。而傅索安的情况却是一个例外,这个例外的后面隐藏着一个谜。这个谜,直到傅索安后来离开这个世界后,才在“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的一部分范围内悄然传开;原来,傅索安在从香港返回苏联的途中,待在“西伯利亚人”号货轮上闲得发慌,便去船上的医务室和船医聊天,渐渐混熟了,她便让船医为她“彻底地检查一下身体”。结果在她离船后得出了结论:肝脏疑有肿瘤,估计是恶性。船医当即报告政治委员,政委便火速向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通报了。对外谍报局认为以如下方式处理为宜:
一、不能通知傅索安本人,免得引起情绪波动,加剧病变或者发生其他事情。
二、不送医院治疗,因为如是肝癌,一般说来是回天乏力,即便治愈,傅索安也不能再干特工了,而由于她是中国人,思想和性格又缺乏稳定性,所以难以安排工作岗位和定居地点。
三、先速送往“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安排一份可做可不做的工作,观其病况发展而定,如果良性肿瘤,则可在学校医院动手术治愈,反之,则让其死于学校医院。根据这三条意见,该局有关经办人员使迫不及待地把傅索安打发出莫斯科,连十月革命节的红场庆典也未让她观看。这也是“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校长布特卡少将立刻召见傅索安并亲自安排她的工作的原因。
傅索安被安排进了学校的教官寝室,仍是一人独居一个套间。
由于房间的布局和家具摆设都是统一样式的,所以傅索安一进门就产生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触景生情,这使她想起了恋人黄一煌。于是,她立刻往学校的高级班部打了个电话,询问黄一煌的情况。接电话的是一个傅索安认识的苏联男教官,他不知道傅索安已经重新返校,以为是从外地打进“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的(这是绝对不允许的),被傅索安的神通吓得下意识地说起了俄语,连问傅索安在什么地方。傅索安说明了情况,他才变得热情起来,但一说到黄一煌却又缄口不语。话筒转到了另一个苏联教官手里,他告诉傅索安:黄一煌已经提前毕业,离开“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了。按照规定,从特务学校毕业的学员由克格勃人事管理局负责分配,所以黄一煌去了何处,连布特卡校长也不会知晓。
傅索安挂断电话,失望地叹了一口气,眼前浮出现黄一煌的脸容,耳畔仿佛响起了他那充满男性活力的、带磁性的嗓音,两串泪珠顺着脸颊慢慢地淌了下来。当天晚上,傅索安喝下了一瓶茅台酒,昏昏沉沉地一直躺到次日中午才醒过来。起床以后,她想起应当去图书馆走一趟,便下楼去门卫那里推了辆自行车,骑到那里,刚走进去,一个轮值在此的教官已经认出她了,赶上前来,又是握手又是寒暄,然后向傅索安办移交。
“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的图书馆,在1973年底时有四万册图书,全是中文版,而且都是中国的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分类编码也完全采用中国正规的方式即北京大学图书管理专业所教授的那一套,按英文字母分二十六个大类,每一类里再用数字分小类,每本书再从书名第一个字的四角号码作为著作号。傅索安在她所喜欢阅读的长篇小说“K257书库”里转了一下,发现这里竟收齐了从50年代出版的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即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在内的所有长篇小说,禁不住惊叹道:“这真不容易,即使在中国,现在也不一定有多少图书馆拿得出这么齐全的长篇小说!”
那个教官说:“不单是文艺类的,其他如政治、哲学、经济、医学、机械、建筑、历史、地理等等的中国版图书,这里也都有,据说是从莫斯科的几所大学里搞来凑齐的。”
那教官又向傅索安介绍了三个当时在图书馆帮他的学员,那是三个姑娘,一个来自澳门,一个来自香港,另一个来自中国大陆。
她们在“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的学业已经结束,克格勃人事管理局可能还未为她们找到合适的“下家”,所以暂不分配,让暂留学校,学校便派她们来图书馆帮忙。现在,这三人都成了傅索安的部下。
次日,傅索安正式上任。她对图书馆采取的方针是不管,任其自由运转,自己每天在办公室里看书、饮茶、喝酒。这样过了两个多月,要看的书都翻得差不多了,傅索安陷入了无聊之中,这才想起要和那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姑娘谈谈。一谈之下,傅索安大喜,原来这个名叫胡国瑛的姑娘也是天津人,也是知识青年。傅索安很想立刻和她详细谈谈,但考虑到图书馆里肯定装着窃听器。于是抑制了这个强烈的念头,悄悄约对方晚上到自己寝室喝酒。
当天晚上,胡国瑛来到傅索安寝室。傅索安已经找出窃听器,拆下了电源接头,这样,在监听终端的录音带上留下的便是寂静无声,就像她平时一个人在寝室里闷头大睡一样。两人一边喝酒,一边畅快地聊了起来,傅索安从胡国瑛的叙述中,知晓了这个比她小三岁的同乡的有关情况——胡国瑛是68届初中毕业生,其父在1957年“大鸣大放”时被定为右派分子,解送劳改,期满后因已被原单位开除公职,只得留场就业。这种家庭出身导致胡国瑛只能夹着尾巴做人,在学校里一贯老老实实,“文化大革命”开始也不能参加红卫兵组织,缩在家里“逍遥”。到1969年春天,学校分配她去内蒙古巴扎地区插队落户,她虽有千般不愿,却也无可奈何,只得奉命前往。
胡国瑛插队的生产队,地处中苏边境线附近,距额尔古纳河只有十几公里。以她的性格,在农村自然表现得不错,劳动肯吃苦,也没有其他知青那种偷鸡摸狗等等的劣行,所以被社员们认为是个“那娃”,两年后当上了生产队的仓库保管员。保管员当了一年多,发生了一件大事:那是1972年4月初,生产队开始春播。队里的土地分布在四面八方,各个生产小组分包一个片,完成任务算工分。这样,有的小组为了多挣工分,常常早出晚收工。生产队为让各小组随时能领到种子、化肥,便安排胡国瑛住在仓库里。胡国瑛没日没夜忙碌了几天,弄得疲惫不堪。那天晚上,看看没人来领种子,她想弄点夜宵吃。仓库里有一个电炉,那是经生产队长特许的,让胡国瑛晚上取暖和烧夜宵。平时胡国瑛使用时特别留心,惟恐发生火灾。这天晚上也实在过于劳累了,烧着夜宵不知不觉就坐在一旁睡了过去。她睡得很熟,还做起了梦。忽然听得“劈劈啪啪”的声响,只觉得浑身燥热,睁眼一看,只见眼前已是火焰一片!
胡国瑛惊叫一声,一跃而起,抓起一把笤帚便冲起火处扑打,怎奈那火已燃烧成势,以一把笤帚对付真好比灯蛾扑火,哪里扑得灭,反倒弄得自己身上也冒起了火星。胡国瑛无奈之下,只得夺门而逃。等她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