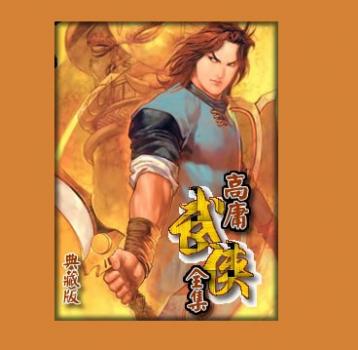血影魔功-第2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颜姑娘一见黄眼无常出手,便知不妙,抽身便退,刚跃退丈余,一个“细胸巧翻云”之式想撒身而退,一面大呼:“席姐姐快走!”
那“五绝神灰”已在半空自开机括,蓬蓬暴射,顿时起了一天灰雾,知道利害,正想以强烈掌风护身而退,满天“菩提珠”恍如星虹百点,破空锐啸而至,方圆十丈之内,尽是黑芒翻飞,只好玉掌翻飞,封住全身,那阵灰雾已匝地涌来,把她笼罩,两条人影,如鹰抓小雀左右夹攻,这一下,颜姑娘即是千手观音,也照顾不及,再听席素雯惊呼一声,全身已沾了灰雾,只觉得混身恍如万针齐刺,又麻、又痛、又辣,四面掌风逼住,奇热灼人,更是难受,竟被两凶生擒过去!
那边席素雯刚闻声欲逃,黑手赛雷公好不快哉,比二凶、三凶下手更疾更辣,一面全力打出“霹雳掌”,把席姑娘僵住,无法脱身、两手一翻,“五绝神灰”也作“十面埋伏”之式打出,把席姑娘前后左右都封住,姑娘大怒,紧咬银牙,不退反进,拼命向大凶抢攻,只听大凶咧嘴细索中空,装有尖芒,破风作怪响,只听对方一声怪笑:“好泼贱,尝下李大爷‘百毒龙爪’的滋味!”
那长爪打出时不过二丈长的乌油细索,头上有拳头大的一个绣球样的东西,忽然在空中暴张开来,竟像一个三角形的大网,下垂数寸长的细丝,活像一个大龙嘴,括的一声,兜头罩下。
席姑娘欲逃不及,刚用“蝶舞虹垂”之式想避开正面,再用“龙飞九天”之式冲出雾阵,右臂已被那些细丝黏住,竟充满了柔中带靭之力,用力一挣,反而收东越紧,挣了两挣,罗袖中裂数道细缝,竟深陷入肉,刚受得着肉处麻辣剧痛,心中一阵迷忽,再闻一声怪笑,便失去了知觉!
第十二章 老怪反常态
等到二女醒来,才知身在石室,耳听外面争吵之声甚烈,竟是四凶都要独占二人为妻,不由羞怒交迸,好得未受捆绑,只有颜姑娘外衣被脱去,席姑娘右臂缠了一块鹿皮,大约上了药。
可是,阵阵腥气,冲鼻欲呕,使得二女同时一愕,游目四顾,不由大骇。
原来,两人虽身处石室,无异一洪荒古洞,阴暗卑湿,四面石壁尖峭嵯列,布满似苓非藤的五颜六色东西,悉悉索索丝丝之声汇为繁响,却在四壁阴暗无光之处,两人穷尽目光一看,竟是一排一排,参差错落,交叠成三角、五角、四方的小铁棚,因势建造,有的利用原来崖隙石洞做成,每条铁丝上涂满了绿色似磷光的东西,有的还七叉八竖着光锐铁蒺藜和倒须钩。里面却爬满了蜈蚣、蝎子等五毒恶物,都是大逾寻常十倍,娱蚣长逾一尺,蝎子大如蒲扇,大约见了生人,美食在前,馋吻怒张,凶睛电射,在黑暗沉沉中集为五彩缤纷的光芒,都有冲网而出之势。
二女虽是艺高胆大,那曾见过这类既大且多的恶形怪状之物,其中有两头大金蝎,头部金黄,背上绿、黄相间,五彩斑烂,更是狞恶,巨口翕张之间,似有淡淡黑气飘浮,知道是成了气候的东西,说不定已有内丹之属,单是那毒气也挡不住,二人同觉得直打嗯心,只不知何故反而醒转了?如普通一般姑娘,岂不吓得尖叫,甚至半死才怪呢!
二女毕竟胆大,一看微映灯光之处有一铁栅门,不过紧闭了一道稀落如核桃大的铁条,宽约五寸左右一根,二女求生心切,正要冒险试试,如能折断一根,便可脱身,再向四凶拼命,作万一之想。
不抖,一阵吱吱怪叫,紧跟数声凄厉的呱呱儿啼,把二女吓得缩身不迭。
原来,两人只见到铁栅门,却未看见门下有一道宽约一丈,长约六尺的暗沟,沟上也蓄着一道铁丝网,吱吱之声,便起自下面,二女目力甚强,已依稀看出下面尽是各种奇形怪状的毒蛇。有些小的已伸出半个蛇头在铁网缝内,红信闪闪,吞吐如电,伸缩之间,活像一把火花明灭不定。最使二女闻声胆裂的是两声呱呱儿啼,起自铁栅门的上端,敢情也有一个大铁笼,翻腾之声甚急且烈,不用说,一定有极大毒蛇怪物锢闭其中,怒极发戒,强行冲击!
二女饶是胆大,也觉头皮发炸,肌皮起粟,相顾失色。
正在进退维谷,全身冷汗,生死两难,急得要命的当儿,只听后洞深处传出一声刺耳急啸,外面四凶争吵之声立止,只听大凶李横低声怒喝:“还闹个鸟,把老家伙骚动了,叫咱们都去哩!都是老四不听话,一只老鼠打坏一锅汤,可是要吃苦头!”
另一个较缓而冷的声音接口道:“老大!你也一变常态,管这两个臭丫头任是怎么美煞,何值自家兄弟伤了和气,还是去请师傅公断吧!老三、老四!去把两个丫头一同带去,由师傅一言而决!”
只听咕噜道:“这两个嫩雏儿原是俺老三到口的馒头嘛,别说老大,便是师傅也要讲理呀……”
只听一声断喝:“休再罗苏吧!别羊肉吃不着,惹了一身膻……”
又听那李横骂道:“别现世啦!若非俺和老二及时赶到,还有命在也只有三分气,忘了喊臭丫头做姑奶奶……”
脚步暴响,大约是三凶和四凶赌气到这边来了。
果然,只听一声吹灯低鸣,不但呱呱、儿啼之声立止,连越来越厉的悉悉、索索、丝丝之声也寂然不闻,一声哗啷啷,铁栅门自动向一边石缝缩进。
二女稍定紧张,一听他们对话,便知是要带自己两人去见他们师傅,听说中条四凶原有一个孽师,又拜在桑老怪门下,不知是要去见那一个,反正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一死不足惜,却怕被桑老怪先吸血,再喝脑髓,然后开膛取心肝,都不约而同的打着拼得一个够本,拼得两个是赚一个的主意,都运功两掌,准备对方一现身,便全力出击,打对方一方一个措手不及。
不料,二女四目,正注视门口,却半晌不见人影。只听洞外壁上翻腾之声又起,又是呱呱两声儿啼,两人不由心中一紧,泛凉意,正犹豫不决,想先冲出门口再说的当儿,两声怪笑过处,呱呱!洞口先闪电般伸出一颗奇扁的大蛇头来,足有笆斗般大,凶睛一对,大如酒盅,绿光泛蓝,闪烁不定,灰中透麻的三角扁头,上有三寸许的一只独角,两腮鼓涨,红信暴伸尺许,腥涎四流,一伸一缩,直把二女吓得倒退三步,摇摇欲倒。
只听一声乾笑,先由洞侧露出黄眼无常的半边脑袋,几乎和那蛇头并排而伸,听他嘻嘻得意的叫:“二位姑娘,休得害怕!这孽畜虽利害,有咱们咧!只要二位好好听话,跟着咱们去见师傅,决不难为你俩,一切有俺保险,决不有损你半根毛发!”
又是呱呱两声,好像和他说话。红信伸缩更急,似欲向二女冲来大啖一顿。只听那尤沌急道:“老三!别废话了!这畜牲好不野性,俺竟制它不住,你快帮着,若致它挣脱,可不是要的!”语音低而急骤,显然,那厮吃力非常,还有三分惊慌。
只听外面一声低暍:“没用的脓包,连这畜牲也制服不了!滚开!仍放到笼内去,休得吓坏她们!如仗着畜牲向她俩示威的话,不如早把她们捆成棕子……”
二女刚听出是大凶李横口音,三凶史了翁的脑袋已不见,那颗大头,也似受了大力量的拉扯,被牵了转去,摇晃未定,那大凶已大模大样的叉手站在门口,竭力装作漫和的口气道:“二位姑娘,不要怕,咱们决不伤害你俩!乖乖同去见咱们师傅,只要不倔强,保有好处给你!”猛的一伸右臂,由壁边夹紧那怪蛇七寸,左掌起处,已在它那扁头上打了一掌,骂道:“你这畜牲!发什么威!若吓坏了两位姑娘,不把你碎割下酒才怪!”
说也奇怪!那畜牲立时变成了烂黄鳝,再也不敢倔强,懒洋洋的由大凶抓紧,动也不动。
洞底深处,又传来一声急啸,只见大凶把它往脚边一甩,叫:“把它关进去!”又向二女挥手:“随着来吧!别自讨苦吃!罚酒是不好吃的!”竟自转身先走。
二女各换了一下眼色,双双跃出,挺身道:“休得无礼!姑娘虽死不可辱!估量着我们的师傅和父亲吧……”
李横冷笑一声道:“老实点!别人怕昆仑和颜老贼,咱们却是牛大还有刮牛法,从小卖蒸饺,什么都见过……”
那尤沌急忙接腔,三句不离本行,好粗:“爹开洗澡铺,娘做接生婆,大大见得多,吓倒咱个鸟!”
史了翁想在美人面前讨好,向尤沌翻了一眼,咕哝道:“俺说二位姑娘,既开饭店,不怕大肚汉,咱们兄弟从不怕过谁来。二位如将就将就,咱们决不亏待你俩。人家说什么大丈夫要权,小丈夫要钱,咱们这些……这些凶丈夫呀只知要……要姑娘,桀!桀!”
他夹七夹八乱念三字经,不伦不类,冒充斯文,却自以为措词得体,盖过老大和老四,黄眼珠骨碌碌乱转,咭咭咕咕傻笑。
颜姑娘恨不得塞了耳朵,看都不看他们一眼,被李横催着快走,几次想硬拼,都被席素雯眼色止住,并冷笑道:“鸭子死了!嘴壳还是硬的,姑奶奶也没有废话同你们说的……”脸容一板,冷笑前行。
史、尤二人急忙由侧而前,在前带路,霉湿腥臭之气,刺鼻欲呕,崎岖凹凸,无处平坦,又黑又暗,阴风惨惨,常人进去,只有初一拜年拜到大除夕,一步十八跌,何止寸步难行?以二女武功,如非有二凶在前出声提醒,随时招呼,也有撞跌之虞。
有的地方要侧身而进,有的地方要低头而入,有的地方要先伸进两腿,有的地方要头下脚上,三凶似乎轻车熟路,不当一回事,却把二女憋得一身香汗,娇喘吁吁,一因呼吸不惯两种恶腥气味,二来心中有着本能的紧张,再加上时闻前后、左右都有刺耳的异声,显然都是蛇虫之类恶物藏身潜伏之所,更增惊骇,真有生不如死之感。
凭着一行脚力,走了半个时辰才由“九折天梯”转进一个伏身而进的小洞,二女已是秀发混乱如鸡窝,衣裙起皱,涂遍污泥灰垢,仍掩不了两张俏脸儿,一白一黑,相映如花。
一人迎面接着,正是那娄元,敢情他先来了?把她俩带到一大堆绿火前,当二女一眼看到大马金刀,盘坐入定的桑老怪时,几乎失声惊叫。
四凶个个肃然,脸都死板板的必恭必敬,在老怪面前一字跪下礼拜,碰头有声,由李横足恭跪禀:“师尊,已把来货带到,恭聆训谕……”对二女一摆手道:“火速跪下听命!”
二女大怒柳眉倒竖,便要拼命!猛地,同时打了一个寒噤,原来老怪睁眼绿光暴射,竟把二女身形照得碧阴阴的,侧恻乾笑一声道:“娃娃,休得倔强,你俩来历,俺已晓得了。便是你俩师傅,见了俺老人家,也不敢无礼。也罢,念你俩娇小可怜,地上不净,免跪!”鼻中哼了一声道:“俺老人家特降殊恩,问你俩人爱着俺四个徒弟内那两个?由俺作主,别瞧这儿并无花团锦簇,只要你俩答应婚嫁,俺老人家敢说你俩要什么就有什么,皇帝想要想不到的东西都可给你俩弄了来……。”
颜姑娘那里听得入耳,气得银牙紧咬,娇躯发颤,正要发作,却被席姑娘在肘上轻碰了一下,只听她冷笑道:“你大约就是绿袍魑魍桑羊……” “了”字尚未出口,李横等已同声低喝:“住嘴,咱们师尊名讳岂是你俩可以乱叫的么?……”
不料,老怪先是绿光暴射,但旋即闭住,反而很和缓的一字一句:“正是俺老人家,想你俩也早听师傅和阿爹说过,可知俺老人家的脾气么?快说……”
末两字如平地一声雷,震得四面壁石都在摇晃,似要崩塌。
席姑娘愤然道:“管你是人是鬼,总不能伤天害理,彼此素昧平生,道不同不相与谋,婚姻大事,岂可儿戏!讲什么……”她原脱口想说“讲什么爱不爱?”但明眸一转,立即加重语气:“即使你为门下作主,不分是非曲直,也要先徵得我师门和尊长同意嘛!”
这几句话,席姑娘可说煞费苦心,含垢忍辱,以落到这般地步,白死无益。硬拼要命,隋珠弹雀,太不值得。所以才委屈陈词。
那桑老怪却多瓜缠到茄子上去,前半段话使他凶睛怒睁,便要发作,倒先把四凶吓得不知如何是好?知道老怪一动手,二女绝无幸理,眼看玉笑珠香,粉滴搓酥搓的两个美人会被老怪吸血破,又不敢出手阻障,都凶不起来了。及见老怪目光又阖,冷哼一声道:“原来你俩是要讲什么乌礼法,先请媒人去向你俩师长说亲,再纳礼下聘,明媒正娶,吹吹打打坐大花轿,哭哭啼啼做新嫁娘么?这也不怪!在这洞内做新房,又无人得知俺老人家门下娶媳妇,太不光釆。再说他们四个,你俩个,岂非乌的乱伦,